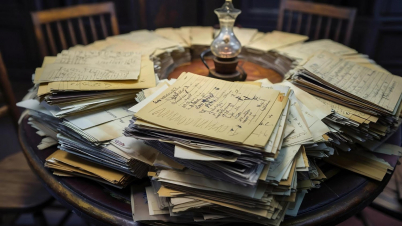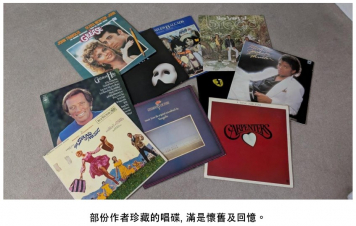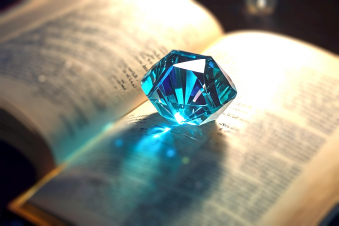受害者被指為「國內恐怖分子」
我曾經對一些教會說:「如果你邀請我講道或者開講座的話,活動完畢之後,我恐怕有一半甚至以上的會友從此失蹤。」最近發生在明尼蘇達州的兩宗槍擊事件,無疑是美國執法爭議與宗教道德辯論的轉折點。若果我有機會就此題目發表演講,我絕不會含糊其辭。我情願有一半人離開,也不願意教會墮入「平庸之惡」。
這次爭論的核心始於連續兩次由ICE(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探員槍殺美國公民的事件。1月7日,37歲的美國公民古德(Renee Nicole Good)在車內遭探員擊斃;儘管國土安全部(DHS)聲稱她企圖衝撞探員,但隨後多間媒體公開的錄影卻顯示,探員開槍時並無即時生命危險。1月24日,退伍軍人醫院ICU護士普雷蒂(Alex Pretti)在抗議現場遭擊斃,多段視頻揭露他當時並沒有做出取槍或威脅性動作。面對這些指控,特朗普總統、萬斯副總統、ICE局長均為探員強力辯護,甚至稱受害者為「國內恐怖分子」,並強調執法人員應享有「絕對豁免權」。
在案發時普雷蒂持有合法槍械,但特朗普多次表達示威者不應該帶槍進入示威現場,這說法引起了全國步槍協會(NRA)和持槍權活動家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攜槍權不應因為參與示威而被取消。最諷刺的是,在1月6號的國會暴動中,有些特朗普支持者都是攜帶槍械進入示威現場。
普雷蒂是否暴力和抵死?
有一段視頻顯示:1月13日普雷蒂向一輛緩慢行駛的執法人員車輛大聲喊叫並吐痰,隨後用力踢碎了該車的後尾燈。支持執法部門的人士認為這證明普雷蒂具有攻擊性;而他的家屬和代表律師(包括曾參與喬治‧弗洛伊德案的律師)則強調,11天前踢車的行為絕不能成為1月24日他在未構成威脅的情況下被射殺的正當理由。
支持ICE做法的人暗示普雷蒂是一個暴力且「抵死」的人。這種手法讓我們想起了幾年前的喬治‧弗洛伊德案。幾年前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員跪頸至死,挑起了波瀾壯闊的「黑命貴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在運動中弗洛伊德被塑造成天使的形象,而反對運動者不斷強調弗洛伊德並非「天使」,而是一個案底纍纍的積犯,試圖以此削弱大眾對警察暴行的憤怒。然而,這些人忽視了一個文明社會最根本的法理原則:正義並非只為「天使」服務。 無論弗洛伊德過去犯過多少次法,無論普雷蒂在11天前是否踢過執勤車輛,這都不構成執法人員可以「就地正法」的理由。保護一個「不完美」的公民免受非法殺戮,這才是法治對公義最嚴肅的承諾。
如果我們接受「因為受害者有污點,所以過度武力可以被原諒」的邏輯,我們實際上是在允許執法部門擁有無視憲法的「處決權」。這種邏輯的終點,便是法治的徹底崩潰。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反毒戰爭」就是最慘痛的教訓,他上台前揚言以鐵腕掃毒,賦予警察近乎無限的武力使用權,暗示只要目標是「壞人」,程序正義便可拋諸腦後。結果是成千上萬的嫌疑人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被處決,其中不乏被烏龍指控的平民與弱勢群體。社會並沒有因此變得更安全,反而陷入了無盡的恐慌中。杜特爾特離任後隨即面臨國際刑事法院對其「危害人類罪」的追究,這證明了任何試圖超越法律的執法,最終都將被正義審判。
其他踐踏人權的案件
除了致命槍擊案,ICE的其他執法行為同樣令人心碎。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名美國公民羅曼(Aliya Rahman )在前往醫院就診腦傷途中,被多名蒙面探員強行拖出車外。儘管她不斷尖叫提醒探員自己是殘疾人士,探員仍擊碎車窗並將其拖行至地,且完全忽視她對輔助器材的需求。《紐約郵報》以大字標題去指出羅曼參加過LGBT和「黑命貴運動」,在報道中將她「起底」。到底她的思想是否激進和探員對她粗暴有什麼關係呢??
而在聖保羅市,56歲的苗族裔美籍公民 ChongLy Scott Thao 在家中遭到ICE闖入。探員在持槍恐嚇後,將僅穿著內褲、披著一條孫子的小毯子的他強行帶往戶外,當時室外氣溫僅有 華氏14度(約攝氏零下10度)。事後證明,這完全是一場認錯人的「烏龍抓捕」。這種踐踏人權的行為,竟然出現在美國!現在美國有何道德高地去指責違反人權的國家?
基督教的撕裂
在美國基督教界,最近的槍擊事件再一次引起了撕裂。自由派與主流宗派,如聖公會(Episcopal Church)和聯合基督教會(UCC),對此表達了最激烈的反對。明尼蘇達州主教盧拿(Craig Loya)公開形容ICE的行動是「冷酷的虐待」,並將其比喻為聖經中希律王的暴政。天主教聖保羅及明尼阿波利斯總教區總主教哈達(Bernard Hebda )亦為死者舉行追思彌撒,呼籲信徒捍衛生命尊嚴。
與此相對,許多保守派福音派人士則採取支持或辯護的立場。副總統萬斯更引用「基督教價值觀」,主張保護國土安全是最高的人道主義,並指責抗議的教會領袖過於意識形態化。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SBC)的態度。美南浸信會領袖在1月7日古德被殺後的數日內,並未發表任何顯著的公開聲明予以譴責。
1月18日,有示威者闖入聖保羅市的城市教會打斷禮拜(因為該教會的一位牧師同時是 ICE的地方官員),保守派領袖對此極為憤怒,稱其為「對宗教自由的侵犯」。截至1月27日,SBC主席普雷斯利(Clint Pressley)及SBC官方媒體均未對普雷蒂遭擊斃一事發表實質性的評論。普雷斯利的社交媒體聚焦於譴責1月18日抗議者闖入城市教會,但對於兩起致命槍擊案或ICE執法權擴張的系統性問題,卻始終隻字未提。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教授莫勒(Albert Mohler)在他的社交媒體平台上認為明尼阿波利斯事件的真相是「令人混淆」,他說:「這並非執法部門故意製造的混亂,而是組織嚴密的左派活動人士故意製造的混亂。」他並強調要尊重法治,要支持聯邦執法人員,他同時批評了抗議活動,這是典型的一切問題歸咎「左膠」。
歷史的教訓
若果翻查歷史,你便會發覺美南浸信會在這些事件中的保守態度是不足為奇的。美南浸信會成立於1845年,其成立的根本原因在於教會內部就奴隸主是否可以擔任傳教士的問題產生了分歧。1844年,阿拉巴馬州浸信會向浸信會海外宣教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訴求(即「阿拉巴馬決議」),他們認為奴隸主有資格被任命為宣教師。該提議遭到拒絕,於是乎,南方各州的代表於1845年5月在喬治亞州舉行會議,他們正式退出海外宣教委員會,並成立了美南浸信會。雖然在1995年美南浸信會為從前對黑奴制度的立場道歉,但這足足遲了150年,稱之為「後知後覺」已算是客氣了!
「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源自鄂蘭(Hannah Arendt)對納粹官員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觀察,強調的是那種「不思考、不批判、僅執行職責」的平庸性。不過,美南浸信會在1845年的反應,其性質可能已經超越了「平庸」,而更接近於一種「主動的意識形態合謀」。1845年,他們拒絕接受北方浸信會對奴隸制的譴責,主動從原有的組織中分裂出來,以保護奴隸主宣教的權利。當時的領袖們並非「缺乏思考」,而是發展出一套極其精密的「親奴隸制神學」(Pro-slavery Theology)。他們利用聖經(如保羅書信中關於僕人服從主人的部分)來將不公義的制度「神聖化」。在今天,很多基督教領袖亦已經超越了「平庸」,例如主持《公民廣場》的林修榮,不斷主動地為特朗普提供宗教與道德背書,維持與當權者的聯盟,已經優先於對公義與受難生命的關懷。
「任由他們離開吧!」
當前,面對ICE在明尼蘇達州連續殺害美國公民的暴行和特朗普的其他倒行逆施(例如侮辱和恐嚇盟友),許多教會領袖選擇了沈默。這種沈默背後的潛台詞是:「若果發聲的話,恐怕會眾會大量流失,甚至教會分裂。」 但這正是「平庸之惡」的溫床:當我們為了維持現狀而放棄道德判斷,沈默就成了暴政的燃料。
對於那些可能要離去的人,我的回應是:「任由他們離開吧!」 一個為了維持人數而閹割真理的教會,早已不再是基督的身體,而僅僅是一個社交俱樂部。難道「豐盛的生命」就是拿了天堂門券之後,擁抱謊言和對受害者麻木不仁的生命嗎?
我們所追隨的耶穌基督,從來不是一個尋求共識的調停者。他在聖殿中憤怒地推翻兌換銀錢者的桌子,直言不諱地斥責當權的法利賽人是「粉飾的墳墓」。他從不害怕得罪建制,因為他的使命不是維持跟隨者的人數,而是彰顯上帝的公義。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膨脹的血腥年代,卡薩斯 (Bartolomé de las Casas)和蒙特西諾斯 (Antonio de Montesinos)等神父、修士在講壇上批判殖民者的罪惡,儘管這些言論令他們孤立;1960年代,馬丁路德金的講道同樣讓無數「溫和派」白人教會感到極度不適,筆者在明尼蘇達州讀書的時候,曾經有一位經歷過民權運動時代的教授說:在馬丁路德金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前,他在美國極不受歡迎,因為無論他去到哪裏都會出現示威活動。
最終的問題是:到底教會是敬拜神,還是敬拜特朗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