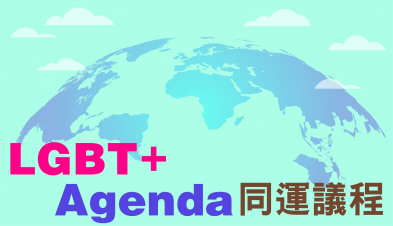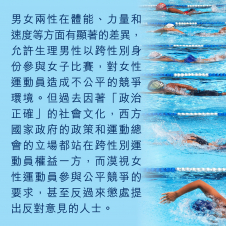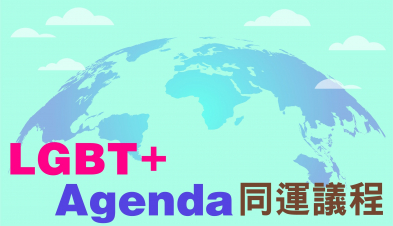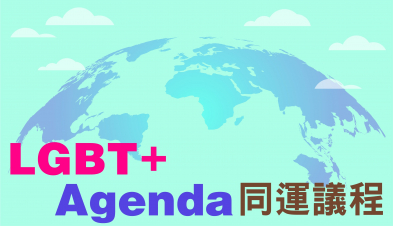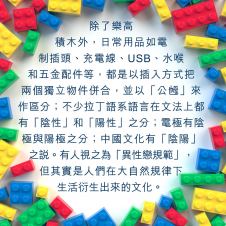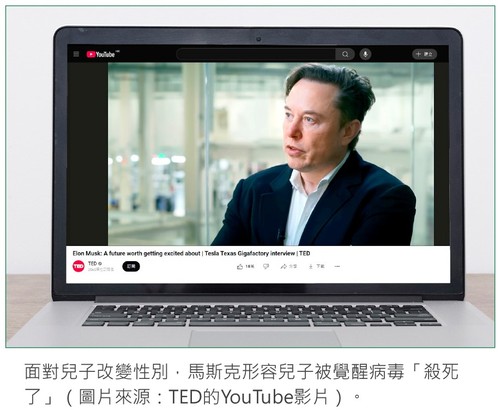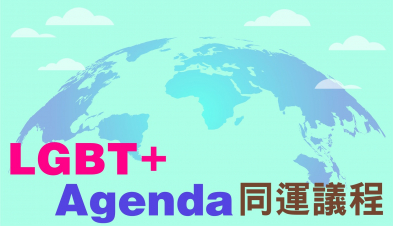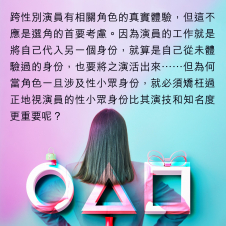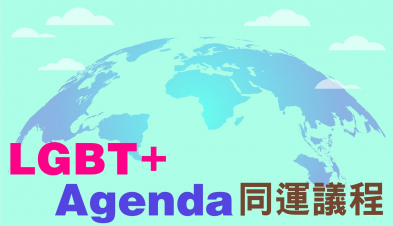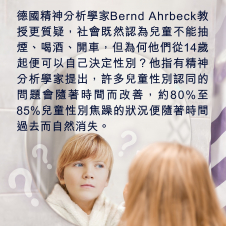美國
多元化、公平、包容(DEI)計劃及聯邦撥款
特朗普在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國總統,在就職禮舉行的當日,特朗普簽署一連串行政命令,當中有針對「性別意識形態的極端主義」。指美國只承認兩種生理性別——男性與女性,並結束聯邦政府內部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計劃,並稱之為「激進和浪費」。其後,他亦威脅要削減對教育機構涉及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DEI)計劃及跨性別政策等議題的聯邦撥款。[1]
1月30日,有多個學區的聯盟組織和代表發表聲明,拒絕執行特朗普政府在1月29日發出的行政命令,他們認為有關行政命令將跨性別身份標記為「反美國的意識形態」,甚至威脅要刑事檢控那些支持學生嘗試更改性別標記的教師。有關組織認為該行政命令是歧視跨性別學生,也有學校職員明確表示,不會遵守當中的內容,又稱會繼續致力於保護跨性別學生的權利。[2]
2月5日,特朗普簽署了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別女性及女孩參與女子運動項目,並且指示聯邦政府開始執法,對不遵守規定的學校切斷資助。另外,特朗普又表明會指示國土安全部長,如遇到有男性試圖以女性運動員的身份申請來美國的簽證,一律拒絕其申請。[3]
美國政府先後審查不同學枚的撥款: 3月31日,審查了哈佛大學及其附屬機構與聯邦政府之間價值2.556億美元的合約,以及價值87億美元的多年期撥款承諾。[4] 4月11日,美國政府採取行動,教育部宣佈切斷對緬因州公立學校所有聯邦資助,同日,一名聯邦法官發佈了臨時限制令,禁止農業部切斷對緬因州部份項目的聯邦資助。[5] 9月政府致函紐約市的公立學校,要求在最後期限前修改支持跨性別政策,否則將取消資助。[6] 紐約市學校在10月16日起訴聯邦教育官員,因他們決定停止向這些學校提供 4,700 萬美元的承諾撥款。[7]
美國地區法院法官Jon Tigar的裁決,阻止特朗普總統及其政府在發放聯邦撥款資助時加入條款,以實施反對多元化及反對跨性別者的行政命令。Tigar在6月9日表示,聯邦政府不得強迫受資助者停止推動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計劃,或要求受資助者停止一些肯定跨性別者存在的計劃。他進一步指出,行政部門製定的議程,當中包括了聯邦資助的領域,仍是受憲法約束,並指政府不得將國會撥款武器化,對受保護的群體施加不公平待遇,或壓制政府不認同或視為危險的思想。[8]
荷爾蒙治療及更正治療
1月28日,特朗普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旨在限制19歲以下人士接受與變性相關的醫療服務。該行政命令指,聯邦政府將不會資助、贊助、推廣、協助及支持為兒童提供的性別肯定治療。[9] 他又要求把跨性別女性囚犯移送到男子監獄及停止為跨性別囚犯提供性別肯定治療,三名跨性別囚犯為此入稟法院,認為該政策違憲,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區域法院法官Lamberth在2月4日頒佈了臨時禁止令,禁止政府將三名男跨女囚犯移送到男子監獄,法官又要求懲教部門職員,必須讓三名囚犯繼續接受跨性別治療。[10] 12月3日,美國地區法官Victoria Marie Calvert裁定,永久命令喬治亞州繼續向已接受治療的囚犯提供荷爾蒙藥物,並允許其他經醫學診斷需要荷爾蒙治療的囚犯開始接受治療。[11]
2月4日,有跨性別兒童的家庭入稟聯邦法院,要求阻止限制兒童接受跨性別治療的行政命令實施。他們希望法院可以盡快頒佈臨時限制令,讓醫院可以盡早恢復提供相關的治療。[12]
2019年,科羅拉多州頒佈了《未成年人轉化治療禁令》,禁止精神健康專家使用試圖改變個人性取向或性別認同的「更正治療」(包括談話療法),違例者將面臨最高5,000美元罰款,並可能被暫停執業資格或吊銷執照。2022年,基督徒輔導員Kaley Chiles因希望與年輕患者就性別焦慮和性取向議題進行對話,於是對州政府提起訴訟。她指控該禁令基於觀點立場和談話內容審查其與患者的交流,侵犯了自身的言論自由權利。Chiles請求法院頒佈命令,禁止科羅拉多州對其執行該禁令。
科羅拉多州在法庭文件中回應,該州尚未對Chiles或任何其他持牌治療師採取違反禁令的紀律處分,並聲稱Chiles擬提供的談話療法並不違法——因她已明確表示不會尋求改變患者的性別認同或性取向。聯邦地區法院允許Chiles繼續進行訴訟,但最終判其敗訴,認為科羅拉多州的法例是要規範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專業執業行為」,而非限制言論自由;法院同時裁定,該州有合法理據保護未成年人免受「有害且無效」的治療。Chiles隨後提出上訴,2025年10月,最高法院維持了地區法院的判決,裁定科羅拉多州的法例僅禁止精神健康專業人士實施「更正治療」,其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屬於附帶性質,且該附帶限制並不違反言論自由原則。[13]
2025年11月12日,美國天主教主教團投票通過決議,正式禁止天主教醫院為跨性別患者提供性別肯定醫療服務。[14]
護照政策
加州網紅男跨女跨性別者Zaya Perysian在1月底收到郵寄給他的新護照,其護照列出了他的生理性別——男性。他偕同其他六名跨性別者和非二元性別者在2月7日提出訴訟,指有關政策違憲。政府辯稱,該政策並不構成非法的性別歧視,也沒有限制跨性別者出國旅行,並提到有關的行政命令重要地指出,性別的不明確定義破壞了「長期以來備受珍視的合法權利和價值觀」。6月17日,美國地區法官Julia Kobick作出裁決,允許需要申請或更新護照的跨性別者及非二元性別者,在性別標註中自主選擇「男性」、「女性」或「X」,而不再受限於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9月19日,特朗普政府向要求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請求允許實施原定的護照性別標註政策。[15] 11月6日,美國最高法院批准特朗普政府的緊急申請,允許執行新護照政策:性別標記僅限「男性」或「女性」,並以出生時的性別為準,推翻拜登時代允許選擇「X」或自選性別的政策。[16].
跨性別軍人
1月27日,特朗普簽署了幾項有關軍隊的行政命令,禁止已入伍的跨性別軍人獲得與性別轉換相關的醫療福利。[17] 美國國防部長Pete Hegseth在2月7日發佈備忘錄,有關文件在2月10日公開,文件指軍隊將不再接納跨性別者的入伍申請,並將會關閉涉及轉變性別的醫療設施。[18]
3月,華盛頓州塔科馬的地區法官Benjamin Settle發佈了一項臨時禁令,暫緩軍方執行特朗普總統之前發出的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別者在軍隊服役。特朗普政府對Settle的裁決提出上訴,並要求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上訴期間擱置Settle的裁決。3 月 31 日,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政府的要求。[19]
逆向歧視
2015年Obergefell案裁定同性婚姻為憲法權利,全美合法化。肯塔基書記員Kim Davis以宗教信仰拒為同性伴侶Ermold與Moore簽發執照,遭判藐視法庭入獄。Davis其後上訴,2023年第六巡迴法院維持判決,她上訴至最高法院求推翻Obergefell案的裁決。2025年11月10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Davis須付逾36萬美元賠償及律師費。[20]
Charlie Kirk遭殺害
9月10日,美國保守派活動組織「轉折點」聯合創始人Charlie Kirk在猶他谷大學活動中遭槍擊身亡。事發時他正在戶外舉行一場名為「請證明我是錯的」辯論會,邀請學生就其政治與文化觀點進行挑戰,現場聚集了大量聽眾。Kirk生前曾多次公開反對跨性別權利,其組織也曾發起反對跨性別相關醫療服務的集會活動。[21]
其他國家或地區
同性婚姻及人工受孕
泰國的同性婚姻平權法在1月23日生效,成為東南亞第一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22]
3月25日,日本大阪高等法院裁定,日本現時不承認同性婚姻是違反了《憲法》第14條第一款中提出,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以及第24條第二款提出,個人尊嚴和兩性本質上平等的條文。此判決是繼札幌、東京、福岡、名古屋等地方的高等法院後,再多一個高等法院作出相同判決。[23]
2018年,兩名波蘭男子在柏林締結同性婚姻,返回波蘭後遭拒絕登記婚姻轉錄,因當地不允許同性婚姻。2025年11月25日,歐盟法院(CJEU)裁定,成員國須承認其他成員國合法締結的同性婚姻,以保障自由遷徙及家庭生活權,但無義務在本國允許同性婚姻。[24]
12月11日,台灣行政院會議通過《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擴大法律適用範圍,把年滿18歲的未婚女性、已完成結婚登記的女同性配偶納入可接受人工生殖技術的對象。目前該修正草案已提交立法院審議。[25
意大利憲法法院在5月22日裁定,女性同性戀伴侶若在海外透過體外受精(IVF)生育子女,二人在意大利均可在法律上獲承認為孩子的母親,即使她們其中一人與孩子並無血緣關係。[26]
LGB國際
9月20日,來自18個國家與地區(包括澳洲、保加利亞、美國和台灣等地)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組織決定脫離傳統的LGBT運動,宣佈成立「LGB國際」(LGB International)——一個專注於捍衛同性戀者權利的新平台。LGB國際組織主席Frederick Schminke表示,曾經代表同性戀者團體的組織如今「完全致力於性別認同意識形態」,導致同性戀者權利日益被邊緣化。國際男女同性戀協會(ILGA)前領導人對LGB國際組織的成立表示歡迎,稱這是回歸基於生理性別權利保障的必要修正。[27]
逆向歧視
來自英國的Jennifer Melle是一名高級護士,早前拒絕使用女性代名詞來稱呼一位已被定罪的兒童性侵犯者,此人外號是「X先生」,是一名男跨女跨性別者,他因在社群媒體上假扮成少女以引誘男孩與他進行性行為而被判入獄。Melle在當值時以先生稱呼X,對方因而憤怒,並以言語羞辱她,令她受到種族歧視和人身威脅。隨後她更收到醫院的書面警告,並將其轉交給護理和助產士委員會(Nursing and Midwifery Council, NMC)。她被指違反了NMC的行為準則,沒有尊重病人的「首選身份」,也沒有維護「尊重」這項價值觀。Melle表示,她後來被轉到另一個病房工作,實際上是被降級,而她的名字亦從內部系統中被刪除,令她無法申請加班。2025年3月,在基督教法律中心(Christian Legal Centre)支持下,她現在以騷擾、歧視和侵犯人權為理據,向Epsom及St Helier大學醫院協會提出法律訴訟。原定12月初在St Helier大學醫院協會接受聽證,但院方通知她聽證會因「不可預見的情況」及一名委員無法出席而無法進行。[28]
運動
2023年,世界田徑總會(World Athletics)投票通過,禁止經歷過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別運動員參與女子組賽事,並宣佈成立工作小組進一步研究跨性別者參賽的議題。2025年2月10日,該會的工作小組公佈研究結果,指出僅以運動員「是否經歷過男性青春期」作為制定規範的依據是錯誤的。報告補充說:「有新的證據顯示,在青春期開始前,運動表現已存在顯著的差距。」報告又指,兒童時期或青春期前的表現差距,在跑步項目為3%至5%,而在投擲和跳躍項目中的差距則更大。[29] 3月25日,該會主席Sebastian Coe在表示,女運動員很快將要接受一次性基因測試,符合資格者才能參加女子組賽事。Coe表示將草擬新的法規,並尋找一家有能力的供應商,以協助進行非侵入性的臉頰拭子或乾血斑分析的測試。總會希望透過測試,以判斷運動員的生理性別,以保護女子田徑運動。[30]
英格蘭曲棍球協會(England Hockey)在1月8日宣佈了一項新政策,下個賽季開始,協會將禁止跨性別女性運動員參加女子組比賽。為了解決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人士參賽的問題,該會設立了兩個競賽組別:女性組和公開組,後者歡迎所有人,包括跨性別者和非二元性別者參與。新政策於9月1日生效。[31]
該會亦在同日宣佈,會更新女性運動項目的參賽規則。相關的性別議題在體壇早已引發不少爭議,外界除了關注跨性別運動員參賽可能引發問題,近年亦開始關注讓性發育障礙(DSD)運動員參賽會否對其他女性運動員引發不公平的情況。田徑運動未來採用的規則,正朝著一個新的方向進發,規則或會要求,出生時為女性但睪酮水平較高的運動員,與出生時為男性其後轉變為女性的跨性別運動員,遵循相同的準則。[32]
英格蘭足球總會(FA)宣佈由6月1日起,跨性別女性(男跨女人士)將不得參與英格蘭女子足球賽事。英國最高法院於4月時裁定,《平等法》中的「女性」是指「生理女性」,「性別」是指「生理性別」。基於此判決,英足總的律師建議總會改變政策,不再允許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女子足球賽事。[33]
英格蘭和威爾斯板球理事會(The England and Wales Cricket Board, ECB)在5月2日表示,因應英國最高法院在4月作出的裁決,該會已更新了先前的規則,宣佈將徹底禁止男跨女運動員參加在英格蘭和威爾斯舉行,所有級別的女子板球比賽。該會提到:「由即日起,只有生理性別為女性的球員才有資格參加成年女子和女生的板球比賽。跨性別女子和女生可繼續參加公開組和混合組的板球比賽。」[34]
性別二元
2018年,蘇格蘭地方政府計劃在公共委員會中設立女性成員的配額,以提升女性在當中的比例,但政府的法定指引中指出,持有「性別確認證書」(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的跨性別女性也應被視為女性。組織「蘇格蘭婦女」不滿相關指引,認為性別是二元及不可改變,故向蘇格蘭法院提訴。蘇格蘭的法院認同地方政府的說法,指性別不限於生理性別,須涵蓋持有性別確認證書的人士。2024年,組織上訴至英國最高法院。2025年4月16日,最高法院裁定,當地《平等法》中的女性是指生理女性,而跨性別女性則不包括其中。判詞提到,《平等法》列明的性別、女性及男性必須是指生理性別,其他演繹既不連貫也不可行,而持有性別確認證書的跨性別女性不符合有關定義,故蘇格蘭政府發出的指引並不正確。[35]
英國最高法院在4月裁定現行《平等法》中的「性別」僅指生物學上的性別後,英國唯一一位公開了跨性別身份的法官Victoria McCloud於上世紀90年代公開了自己的跨性別身份,並於2006年成為了法官。他向歐洲新聞台(Euronews)表示:「作為一名『擁有』女性生殖器官、數十年前就公開了身份的男跨女人士,現在要求我必須使用男性廁所、男性更衣室,並被當作男性對待,生活對於我這種人來說變得不再可能。」在1998年《人權法案》下,英國是受歐洲人權法院的裁決所約束。McCloud對英國最高法院的裁決提出質疑,已向歐洲人權法院 (ECtHR) 提出申請。[36]
荷爾蒙治療
11月19日,新西蘭宣佈將禁止為跨性別青少年提供青春期阻斷劑的新處方。該禁令已於 12月19日起生效。[37]
[1] “Defending Women from Gender Ideloogy Extremism and Restoring Biological Truth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defending-women-from-gender-ideology-extremism-and-restoring-biological-truth-to-the-federal-government/; “Ending Radical And Wasteful Government DEI Programs And Preferencing,”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ending-radical-and-wasteful-government-dei-programs-and-preferencing/; Kanishka Singh, “Advocates sue to block attempted dismantling of US Education Department,” Reuters. March 25,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advocates-sue-block-attempted-dismantling-us-education-department-2025-03-25/; https://www.usnews.com/news/politics/articles/2025-03-24/advocates-sue-to-block-attempted-dismantling-of-us-education-department.
[2] Erin Reed, “School Systems across US refuse to comply with anti-trans executive order,” Truthout, February 1, 2025. https://truthout.org/articles/school-systems-across-us-refuse-to-comply-with-anti-trans-executive-order/; “Ending Radical Indoctrination in K-12 Schooling,”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9,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ending-radical-indoctrination-in-k-12-schooling/.
[3] “Trump says he will prevent transgender athletes from participating in women’s sports,” Reuters,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trump-says-he-will-prevent-transgender-athletes-participating-womens-sports-2025-01-19/.
[4] Nate Raymond, “Harvard professors sue over Trump’s review of $9 billion in funding,” Reuters. April 14, 2025. https://www.reuters.com/legal/harvard-professors-sue-over-trumps-review-9-billion-funding-2025-04-12/; https://orientaldaily.on.cc/content/%E5%85%A9%E5%B2%B8%E5%9C%8B%E9%9A%9B/odn-20250402-0402_00180_022/%E7%BE%8E%E8%81%AF%E9%82%A6%E6%94%BF%E5%BA%9C%E5%AF%A9%E6%9F%A5%E8%88%87%E5%93%88%E4%BD%9B%E5%A4%A7%E5%AD%B8%E5%90%88%E7%B4%84;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511/8671917.
[5] Leah Douglas, “USDA freezes some funds to Maine over support for transgender athletes,” Reuters. April 3,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usda-freezes-some-funds-maine-over-support-transgender-athletes-secretary-says-2025-04-02/; Nate Raymond, “Maine sues over USDA pause on funds due to support for transgender athletes,” Reuters. April 8, 2025. https://www.reuters.com/legal/maine-sues-over-usda-pause-funds-over-support-transgender-athletes-2025-04-07/; Nate Raymond and Jack Queen, “Maine's school funding over transgender athletes,” Reuters. April 12, 2025. https://www.reuters.com/legal/trump-administration-cannot-freeze-maine-school-lunch-funds-over-transgender-2025-04-12/; https://san.com/cc/usda-freezes-funding-for-maine-programs-over-transgender-athletes/; https://www.aol.com/news/maine-sues-over-usda-pause-172353519.html; https://www.yahoo.com/news/judge-temporarily-blocks-usda-interfering-224800968.html; https://www.nbcnews.com/nbc-out/out-politics-and-policy/trump-administration-investigates-maine-claims-withholding-gender-tran-rcna198617; https://www.movefm.com.au/trump-administration-moves-to-pull-maines-school-funding-over-transgender-athletes-2/.
[6] Carolyn Thompson, “NYC schools sue US education officials over $47M grant cuts tied to transgender policies,” AP, October 17,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transgender-bathrooms-education-department-sc...
[7] The Associated Press, “NYC schools sue US education officials over $47M grant cuts tied to transgender policies,” Newsday, October 16, 2025. https://www.newsday.com/news/nation/transgender-bathrooms-education-depa....
[8] Janie Har, “Judge blocks administration from enforcing anti-diversity and anti-transgender executive orders,” AP, June 10,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trans-rights-dei-6367d501717f1388677e128af277fe26.
[9] Ana Faguy, “Trump signs order restricting gender care for young people,” BBC, January 31, 2025.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5yd97w74l9o; Ayana Archie and Jaclyn Diaz, “Trump signs an order restricting gender-affirming care for people under 19,” NPR, January 29, 2025. https://www.npr.org/2025/01/29/nx-s1-5279092/trump-executive-order-gender-affirming-care; “Donald Trump says he will deny visas for Transgender Olympic Athletes,” Newsweek, February 5, 2025. https://www.newsweek.com/donald-trump-says-he-will-deny-visas-transgender-olympic-athletes-2026896; “CDC Removes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Pages: What Advocates Said,” Newsweek, January 31, 2025. https://www.newsweek.com/cdc-gender-identity-sexual-orientation-website-trump-order-reaction-2024567.
[10] Devan Cole, “Judge blocks federal prison system from moving three transgender women to men’s prisons,” CNN, February 4, 2025. https://edition.cnn.com/2025/02/04/politics/judge-lamberth-trump-transgender-prison-executive-order/index.html; 關伶如:〈分「男、女」關押跨性別者 川普行政令被聯邦法院擋下〉,世界新聞網,2025年2月5日,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468/8530083;Mike Scarcella, Nate Raymond and Luc Cohen, “US judge blocks Trump from sending transgender women to men’s prisons,” Reuters, February 6, 2025. https://www.reuters.com/legal/us-judge-blocks-trump-sending-transgender-women-mens-prisons-2025-02-05/.
[11] Jeff Amy, “Judge orders Georgia to continue hormone therapy for transgender inmates,” AP, December 10,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georgia-transgender-prisons-hormone-therapy-l... “Victory for Trans Rights: Federal Judge Strikes Down Georgia Law Banning Gender Dysphoria Treatment in Prison,” 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 December 3, 2025. https://ccrjustice.org/home/press-center/press-releases/victory-trans-ri....
[12] Brendan Pierson, “Trump administration sued over order banning transgender healthcare for minors,” Reuters, February 5, 2025. https://www.reuters.com/legal/trump-administration-sued-over-order-banning-transgender-healthcare-minors-2025-02-04/; Brendan Pierson, “Trump administration sued over order banning transgender healthcare for minors,” Reuters, February 5, 2025. https://www.reuters.com/legal/trump-administration-sued-over-order-banning-transgender-healthcare-minors-2025-02-04/.
[13] Lawrence Hurley, “Supreme Court skeptical of state bans on conversion therapy aimed at LGBTQ kids,” NBC News, October 7, 2025.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supreme-court/supreme-court-weighs-chal... Melissa Quinn, “Supreme Court wrestles with Colorado counselor’s challenge to “conversion therapy” ban,” CBS News, October 7, 2025. https://www.cbsnews.com/news/supreme-court-arguments-colorado-conversion... Melissa Quinn, “Supreme Court to hear free-speech clash over Colorado “conversion therapy” ban,” CBS News, October 6, 2025. https://www.cbsnews.com/news/supreme-court-lgbtq-free-speech-colorado-co....
[14] Tiffany Stanley, “US bishops officially ban gender-affirming care at Catholic hospitals,” AP, November 13,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us-catholic-bishops-transgender-health-care-i....
[15] Linsay Whitehurst, “Trump asks the Supreme Court to allow him to enforce transgender and nonbinary passport policy, ” AP, September 20,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transgender-nonbinary-passports-a8abef0... Michael Casey, “Judge says government can’t limit passport sex markers for many transgender, nonbinary people, ” AP, June 18,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transgender-passports-nonbinary-trump-policy-....
[16] Lawrence Hurley, “Supreme Court allows Trump to enforce passport restrictions targeting transgender people,” NBC News, November 7, 2025.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supreme-court/supreme-court-allows-trum... Kim Chandler, “Alabama board votes to remove books about being transgender from public library youth sections,” AP, November 21,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libraries-transgender-books-8f96ee2564c8e4858....
[17] “Prioritizing Military Excellence and Readiness,”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7,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prioritizing-military-excellence-and-readiness/; 石秀娟:〈川普重整美軍 檢討跨性別者從軍、廢DEI多元政策〉,中央通訊社,2025年1月28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501280114.aspx。
[18] “Pentagon to ban trans people from joining military, pauses gender-transition procedures,” NBC News,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nbcnews.com/nbc-out/out-politics-and-policy/pentagon-ban-trans-people-joining-military-pauses-gender-transition-pr-rcna191569; Idrees Ali, Phil Stewart and Luc Cohen, “US judge asks for assurances for transgender service members who sued over Trump order,” Reuters, February 5,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us-military-trying-remove-transgender-service-members-legal-filing-says-2025-02-04/; Jo Yurcaba and Garrett Haake, “Trump signs executive order barring transgender people from military service,” NBC News. January 28, 2025, https://www.nbcnews.com/nbc-out/out-politics-and-policy/trump-executive-order-transgender-military-dei-rcna189470.
[19] Luc Cohen, “Appeals court won’t delay block on US military’s transgender ban,” Reuters. April 1,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appeals-court-wont-delay-block-us-militarys-transgender-ban-2025-04-01/.
[20] Andrew Chung, “US Supreme Court rejects bid to overturn same-sex marriage right,” Reuters, November 11,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supreme-court-rejects-bid-overturn-same... Melissa Quinn, “Supreme Court rejects bid to overturn landmark same-sex marriage decision,” CBS News, November 10, 2025. https://www.cbsnews.com/news/supreme-court-rejects-bid-to-reconsider-lan...
[21] Melissa Quinn et al., “Charlie Kirk shooting suspect in custody after manhunt; Erika Kirk vows to keep holding Turning Point USA events,” CBS News, September 13, 2025. https://www.cbsnews.com/live-updates/charlie-kirk-shot-utah-turning-poin... Helen Coster and Maria Tsvetkova, “Charlie Kirk’s rhetoric inspired supporters, enraged foes,” Reuters, September 13,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charlie-kirks-rhetoric-inspired-support....
[22] “What to know about Thailand’s same-sex marriage law,” Reuters. January 23,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thailands-same-sex-marriage-law-2025-01-23/.
[23] 〈大阪高院裁定 不承認同性婚姻是「違憲」〉,《自由時報》,2025年3月25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4991040。
[24] Should be recognised throughout bloc,” Reuters, November 26,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eu-court-says-same-sex-marriage-sho....
[25] 〈台灣擬准女同婚者人工生殖〉,《明報新聞報》,2025年12月13日。
[26] Claudia Greco, “Lesbian mothers win legal status in Italy IVF ruling,” NBC News. May 23, 2025. https://www.nbcnews.com/nbc-out/out-news/lesbian-mothers-win-legal-status-italy-ivf-ruling-rcna208623.
[27] “LGB 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organizations separate from the LGBT movement,” LA DERECHA DIARIO, September 21, https://derechadiario.com.ar/us/argentina/lgb-international-gay-and-lesb... Nicole Winfield, “LGBTQ+ Catholics make Holy Year pilgrimage to Rome and celebrate a new feeling of welcome,” AP, September 7,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vatican-pope-lgbtq-197507e47890e2e5115a7f784d....
[28] Sami Quadri, “Christian nurse takes legal action after NHS 'punished' her for calling transgender paedophile ‘Mr’.” The Standard. March 23, 2025. https://www.standard.co.uk/news/london/south-london-nurse-legal-action-nhs-transgender-row-b1218290.html; Jo Faragher, “Disciplinary hearing cancelled in NHS misgendering case,” Personnel Today, December 10, 2025. https://www.personneltoday.com/hr/nhs-misgendering-case-jennifer-melle/
[29] “World Athletics planning amendments to female eligibility guidelines,” Reuters,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reuters.com/sports/athletics/world-athletics-planning-amendments-female-eligibility-guidelines-2025-02-10/.
[30] Shrivathsa Sridhar, “World Athletics to introduce genetic tests for women,” Reuters. March 25, 2025. https://www.reuters.com/sports/athletics/world-athletics-introduce-genetic-tests-women-2025-03-25/; https://www.tpenoc.net/news/world-athletics-female-gender-tests/.
[31] “Hockey to ban transgender women from female competition,” Reuters, January 9, 2025. https://www.reuters.com/sports/england-ban-transgender-women-female-competition-2025-01-08/.
[32] Eddie Pells, “Track’s proposed eligibility, transgender rules would completely ban Semenya and others,” AP, February 11,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transgender-semenya-track-364e7e6fc633d48c31b07049a873df26;〈跨性別與DSD運動員或有新規範:世界田徑總會如何平衡公平與包容?〉,《關鍵評論》,2025年2月11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48939。
[33] Rory Sullivan, “Football Association to ban transgender women from women’s football in England,” Euronews, May 1, 2025. https://www.euronews.com/2025/05/01/football-association-to-ban-transgender-women-from-womens-football-in-england.
[34] “Transgender women banned from women’s cricket in England and Wales,” AP, May 2,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cricket-transgender-ban-england-06dd07e6568f086fcb0698cca339666a.
[35] 〈英高院裁定按生理性別定義「女性」〉,《信報財經新聞》,2025年4月17日;〈英國最高法院裁定《平等法》女性定義不包括跨性別女性〉,《NOW新聞》,2025年4月17日。https://news.now.com/home/international/player?newsId=600807;Angus Cochrane, “Supreme Court backs ‘biological’ definition of woman,” BBC, April 16, 2025.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vg7pqzk47zo.
[36] Estelle Nilsson-Julien, “UK's only transgender judge plans to take government to ECHR over biological sex ruling,” Euronews, April 30, 2025.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5/04/30/uks-only-transgender-judge-plans-to-take-government-to-echr-over-biological-sex-ruling; “Legal challenge submitted to Eurpo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on behalf of UK’s first trans judge,” Garden Country Chambers, August 20, 2025. https://gardencourtchambers.co.uk/legal-challenge-to-european-court-of-h....
[37] Reuters, “New Zealand halts new puberty blockers for young transgender people,” NBC News, Nov 20, 2025. https://www.nbcnews.com/world/asia/new-zealand-halts-new-puberty-bloc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