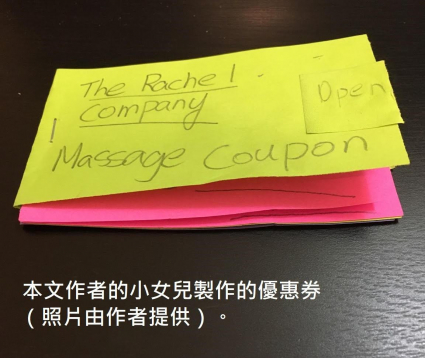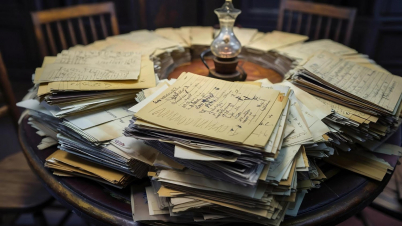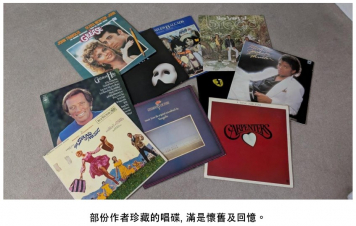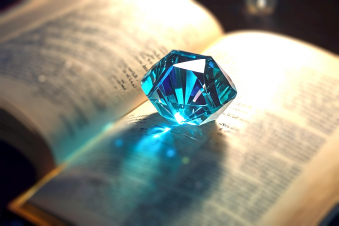在當代社會,大學排名幾乎成為所有持份者的共同追求。對大學行政人員而言,高排名反映出學校的知名度與資源;對教授來說,更多的論文與引用往往直接關乎升遷與江湖地位;對學生與家長而言,能夠進入排名靠前的大學是光宗耀祖。對政府來說,本地大學排名是政績的一部份,例如今年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強調:「香港是全球唯一擁有多達五所百強大學的城市。」
然而,這股競逐排名的風氣卻帶來嚴重的副作用:學術研究的首要目標不再是探索真理,而是滿足排名指標。結果是,大量看似豐碩的學術成果,在歷史長河中可能最終變成了故紙堆,這反而削弱了學術本應有的公共信任。
《撤回觀察》(Retraction Watch )是一個監督組織,專門監察學術出版中的不當行為。它每天與每週都會發布最新消息,這監察組織揭露的學術不端事件數量實在令人震驚,以下只是冰山一角。
舉例說,西班牙研究員伊娃‧卡羅(Eva Carro )是阿茲海默症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截至2025年9月底,其論文在「谷歌學者」 (Google Scholar )上的引用次數已經高達12,688次。她於2009年在學術期刊《神經生物病症》(Neurobiology of Disease)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了某類蛋白質和阿茲海默症的關連。然而,這篇文章在2025年9月被期刊撤稿,撤稿聲明指出,該文重複圖像,有操控數據的嫌疑;而且作者的實驗可能沒有獲得適當的倫理審批。但卡羅未能提供原始數據來證明論文的真實性,她的回應也未能令編輯滿意。其實,這是卡羅的第二次撤稿:她另一篇於2010年發表的論文亦因圖像問題於2021年被撤回。
這是令人感嘆和心寒的事件,阿茲海默症是一種神經退化疾病,屬於最常見的失智症,很多老人都有這風險,研究員若果能夠找出病因和醫治的方法,這無疑是一個福音,但失實的研究結果,不單止給予病人虛假的希望,而且可能會誤導了研究方向,阻礙發展出真正有效的療法。
上述的事件發生在歐洲,但學術造假是全球性的,美國也不例外。2023年,哈佛大學指控前哈佛商學院教授弗朗西斯卡‧吉諾(Francesca Gino)在多篇學術論文中偽造數據和研究不當行為。經過內部調查後,哈佛商學院於將吉諾停職,並於2025年5月撤銷其終身教職。最搞笑的是,吉諾的研究課題之一是為何人們會做出不誠實的行為和怎樣幫助人矯正!在醜聞未爆發之前,人們對吉諾十分敬重,指望她的研究能夠為這個惟利是圖的商業社會匡正風氣,不消說,現在人們已經對她那些宏大的理論信心破產。
吉諾大約有五篇論文被撤稿,相對來說,這算是「小兒科」。根據《撤回觀察》的最新「撤稿排行榜」(更新日期:2025 年 8 月 26 日),德國麻醉科醫師約阿希姆‧博爾特(Joachim Boldt )目前以221篇撤稿位居首位;日本前東邦大學副教授藤井芳孝則有172篇造假論文遭揭發。
除了抄襲或者造假之外,有些學者還會用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去催谷論文數量。在2013年至2014 年間,一份國際學術期刊發現:台灣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陳震遠建立了多達130個假冒身份的電子郵件帳號,用以在出版社的投稿系統為自己的論文做審查,換言之,陳震遠以其創建的假身份審查自己的論文,他當然將自己的文章吹捧得天花龍鳳,結果該期刊撤銷了陳教授六十篇論文。
另一種篤數的手法是變相行賄。在今年5月至8月間,南京一家名為A-Techo的機構向多位期刊編輯發出電子郵件,提出願意為每篇被接受的稿件支付五百至一千美元的「加速處理費」。雖然表面上聲稱是為了支持審稿流程,但編輯很快意識到,這其實是企圖行賄期刊,讓品質低劣的論文獲得刊登。
現在人工智能令傳統的做假手法過時,根據西北大學教授里斯‧理查森(Reese Richardson)與薩里大學教授馬特‧斯皮克(Matt Spick)最近的一項研究,開放存取數據與生成式人工智慧使得撰寫論文變得容易許多,這導致大量低品質的論文湧入學術期刊,這些文章經常引入具誤導性的結果與錯誤的發現。
即使沒有牽涉到不誠實,很多學術論文的可靠性仍然要打上一個大問號。我已經在學術圈子打滾了幾十年,觀察到不少教授和研究人員對研究方法與統計知識理解有限,常常因為訓練不足而採用不當方法或錯誤詮釋資料。很多次我對他們建議採用更精準的數據科學和機械學習方法,但都受到拒絕,理由是他們要迎合學術期刊慣常的做法。
可能讀者會反駁:這無非是你主觀的經驗,但有客觀證據印證我的經驗。2015年有一個大型國際合作專案,嘗試複製一百篇頂尖心理學期刊的實驗結果,結果只有36%成功複製。很多失敗的原因不是造假,而是樣本數不足、統計檢定方法用錯、選擇性報告結果等。學術界稱這種現象為「複製危機」( Replication crisis)。此外,根據一項2017年在《自然》期刊發表的論文,作者詳細檢視了791篇在頂尖學報發表的文章,其中竟然有51%錯誤地解釋統計結果。試想像這個情況:如果電力公司通知你,在過去一年的電費單中,其中有六個月的收費是不正確的,你會接受嗎?
以上一類算是誠實的錯誤。但無論是不誠實還是誠實的錯誤,其負面影響是十分深遠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正如上面提過,因為大學要爭取高排名,排名的條件之一是教授的論文數量和被引用的的數量,而教授能否得到續約和升職,很大程度上倚賴著作。可是,當論文的數量與引用次數壓過研究的嚴謹性與誠信時,許多研究者便傾向於倉促發表、誤用研究方法,甚至抄襲、造假。
現在,爭取排名和催谷論文數量已經不再是大學之間的競爭,而是上升到大國博弈的層面,傳媒多次報道:某東方大國在科研領域的成就已經超過美國,因為其論文的數量和被引用次數現在遙遙領先。我曾經不止一次撰寫文章,去質疑這種指標能否真實地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科研成就。
在這樣的背景下,難怪有人批評美國社會存在反權威、反科學、反智傾向。但另一方面,學術界的種種醜聞,卻真的令人望而卻步、敬而遠之。要建立公眾對學術界的信心,大學真的需要重新檢討對排名和出版的態度,回到追求真理的初心。
新約聖經哥林多前書第三章說:「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這個深刻的告誡,完全適用於我們對學術研究的追求。學術界應以追求真理為至高目標,像匠人打磨寶石一樣,嚴謹地探究、紮實地立論,讓每一項研究成果都成為能夠經受時間檢驗、為人類知識寶庫增添價值的真材實料,而不是短暫的沽名釣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