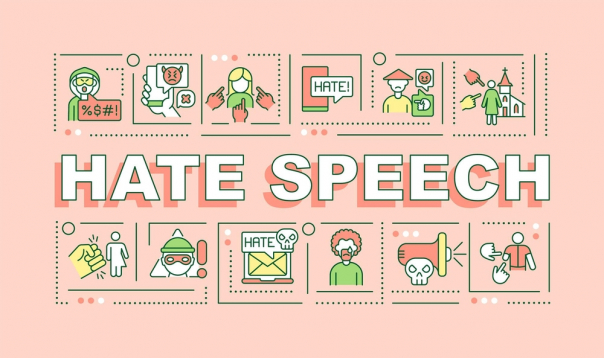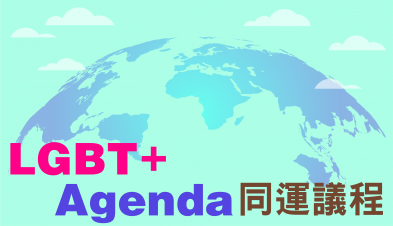在李天命之前的黃展驥
去年底著名香港邏輯學家李天命教授逝世,雖然他沒有撰寫傳統意義的學術著作,但他將邏輯學普及化,這仍然是功不可沒的。不過,在李天命之前,其實還有另一位為大眾解釋邏輯謬誤和推廣思想方法的中文大學教授,他的名字是黃展驥,外號是「謬誤黃」,他的老師是另一位鼎鼎大名的邏輯學家殷海光。我在年少時曾經拜讀黃展驥的作品,例如《謬誤與詭辯》,所以在讀李天命的著作之前,其實筆者已經對很多基本的邏輯謬誤略有所聞,後來我在大學本科和研究院也讀過邏輯學,但都是抽象和艱澀的符號和形式,相對之下,我從黃展驥身上更獲益良多。
令我感到慨嘆的是,不論學歷、不論宗教信仰、不論政治立場、不論人生閱歷,很多基本的邏輯謬誤依然循環不息地在不同場合出現。在這篇短文裏,我想討論一種常見的邏輯陷阱,那就是「稻草人謬誤」(Strawman fallacy)的隱蔽變體:辯論者往往會刻意且隱晦地擴大對方的論點。
總統需要牧師級別的品格嗎?
舉例說,在上一屆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候選人特朗普的品格與誠信受到廣泛質疑,部分強調道德價值的美國福音派領袖便採取了隱晦地擴大論點的辯護策略。例如楊東川牧師在一個由角聲主辦的論壇中提出:現在是選總統,不是選堂會牧師,我們不需要一個品格高尚的聖人。但以我所知,在辯論中對方從來沒有說過總統要具有牧師一樣的道德標準,這只是他所建立出來的「稻草人」,那就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想敵」。
這段論述還隱含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類比」(False analogy),楊牧師將對總統候選人基本品格與公職信用的正當要求,極端化類比為「對宗教領袖或聖人的道德苛求」。事實上,批評者要求的並非牧師般的宗教情操,而是身為大國領袖應具備的基本法治精神與道德底線。他將基本的誠信門檻轉換成了道德頂峰時,原本合理的品格質疑就顯得像是不切實際的政治潔癖,從而成功地繞過了對具體道德缺失的實質討論,讓支持者的立場顯得務實且必要。
大部份自主研發可以為侵權洗白嗎?
這種值得商榷的邏輯,在經濟學家金刻羽教授(Keyu Jin)的訪談及其著作中清晰可見。她在為發展中國家科技企業的侵權與抄襲行為辯護時,常強調那些公司的科技成就主要歸功於應用型創新與龐大市場驅動的自主研發,並主張西方過度放大了早期的「模仿行為」。這種思維的潛台詞是:「你指控我的成功都是靠偷來的,這不能成立,因為我們有很多東西都是自主研發的。」這種辯護是以整體創新去淡化具體侵權爭議,造成對方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2003年思科(Cisco)起訴另一間通訊器材公司的案件是一個好例子,當時筆者正是在思科工作,思科是網路儀器的龍頭,但另一間公司的路由器不僅代碼與思科相似,連操作指令和說明書都幾乎一樣。思科發現自己的程式被抄襲,最確鑿的證據是連思科的原始碼錯誤(Bugs)和拼字錯誤都被一併複製了,當時最具代表性的辯護觀點是:在數百萬行代碼中,被指控抄襲的部分僅佔約 2%,其餘98%皆為自主研發。
然而,這種數據上的比例遊戲誤導了公眾對技術核心的認知,那2%的代碼並非無關緊要的邊緣細節,而是涉及核心功能的路由協議(Routing protocol)與關鍵算法。在知識產權的領域中,侵權的判定不在於字數的佔比,而在於是否竊取了系統的「心臟」。即使原創佔了絕大多數,也無法洗白那關鍵少數代碼對他人勞動成果的實質侵害。其實原告或批評者從未主張對方的成功百分之百源於剽竊,但辯護者仍會試圖將實質性的侵權行為淡化為比例上微不足道的小錯,從而轉移法律與道德上的責任。
大魔頭一定是全然敗壞嗎?
但最令我感到詫異的是,研究邏輯學和倫理學的加拿大哲學家戈維爾(Trudy Govier)也犯上類似的錯誤,她反對將一些千夫所指的罪犯妖魔化,她指出這些人也有人性的一面,她寫道:「他們善待動物和孩子;熱愛葉慈的詩、貝多芬的音樂或康德的道德哲學。一個被起訴的戰犯,例如波斯尼亞塞族領導人卡拉季奇(Karadzic),是一個富有愛心、受過精神醫學教育的人,而且熱愛詩歌;一個集中營指揮官也可以是一位技藝精湛的音樂家。」簡單地說,即使一些窮凶極惡的人也會做一些好事或者具有高級的品味。
這個論證隱藏了一個假設:十惡不赦的大魔頭一定要全然敗壞。其實,一個壞人當然有時候會做好事,但一個人並不需要每時每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惡行,這才算是邪惡。舉個例子說,前南韓總統全斗煥在執政期間實施威權統治,並且發動了臭名昭著的「光州事件」,他有沒有做過好事呢?當然有,他曾經大力發展經濟,在他統治期間,南韓 GDP 年均成長率高達8%,儘管他為南韓帶來高速經濟成長,但這仍然無法洗脫其獨裁者的身份。有趣的是,在20世紀八零年代,香港曾經流行過「英雄片」,所謂英雄片,其實是美化黑社會的電影,在片中,狄龍、周潤發飾演的黑幫頭子都是充滿義氣的英雄好漢。黑社會分子有沒有做過好事呢?當然有,但這仍然無法為黑社會洗白。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利用「人性微光」來擴大指控範圍、進而掩蓋核心罪惡的辯護修辭。
總結
以上所舉出的例子都屬於隱藏性的,但有時候對方擴大自己論點和舉起稻草人卻十分明顯,舉例說,我一貫主張大學課程不應只局限於古典統計學,而是應該將課程內容伸展到數據科學、機械學習、人工智能。反對者說:難道我們可以將所有分析都交給機械學習和人工智能,而不需要古典統計學嗎?這種明顯的擴大論點是十分容易反駁的,其實我從來沒有說過要全盤放棄古典統計學,相反,我認為兩者可以兼容,用那一套要視乎研究之目的和手上有什麼數據。不過,隱藏式的擴大論點、稻草人、類比謬誤則需要小心觀察和分析。
綜上所述,不論是對政治領袖的品格洗白、抄襲技術的辯護、抑或是對邪惡的質疑,這種「隱蔽擴大對方論點」的辯護手法,本質上都是在規避對核心特質的嚴肅審視。辯論者透過建立一個「要求高尚道德」、「大部份或全盤剽竊」、「全然敗壞」的極端稻草人,將原本關於誠信門檻、核心產權、人格底線的討論,轉向對「局部優點」大書特書。邏輯學的普及不僅是為了辨別詭辯,更是為了保護我們不被那些看似理性的「比例遊戲」與「人性微光」所迷惑。在追求真理與公義的過程中,我們要敢於直視某些行為是否已經觸及了文明與道德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