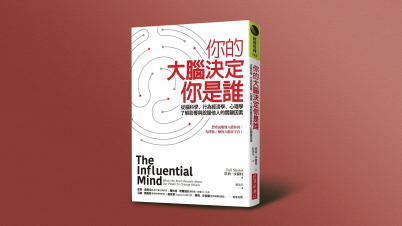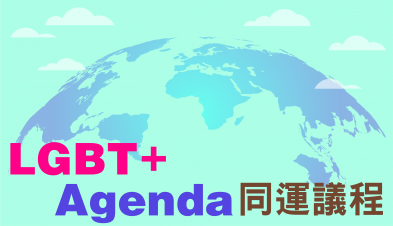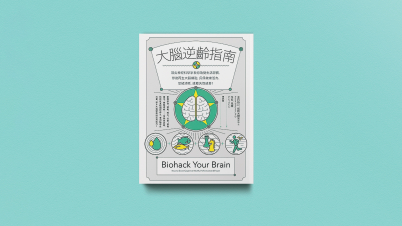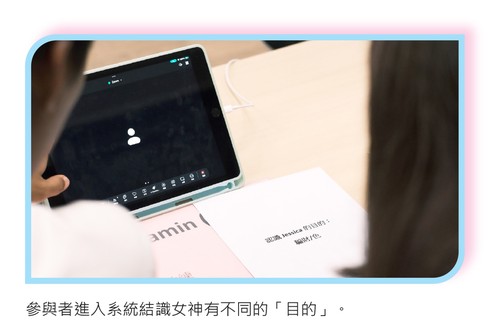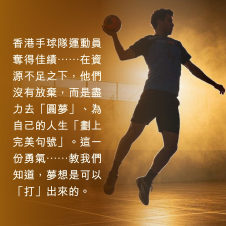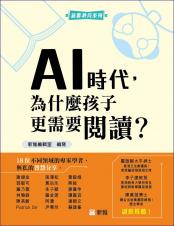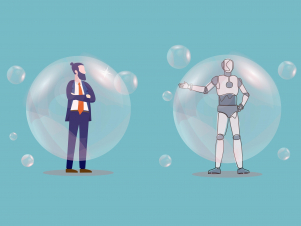受訪者:Janice (眼科醫生)
「我的孩子要贏在起跑線。」這是很多香港父母的意念。孩子還未出生,父母急於籌劃著孩子的將來;孩子還未入讀幼稚園,父母已經張羅幼兒學前預備班,生怕孩子一旦錯過學習時機,便失去與他人競爭的籌碼。這個社會不斷告訴家長:孩子必須成為菁英,因此,即使孩子不是天生的資優兒,父母也希望可以通過大量的培訓,讓孩子不至於落後太多。於是乎,贏在起跑線的孩子在成長路上須時刻保持領先;輸在起跑線的孩子更要奮起直追,在你追我趕的人生賽道,到底有多少孩子可以快樂地成長?他們的獨特之處,真的能被父母看見嗎?那些特殊孩子,又能否彰顯神奇妙可畏的創造?今期我們邀請了眼科醫生Janice,與大家分享她和女兒的故事。Janice的孩子Isla非但不是資優兒,而是一名染色體缺失(22q13.3缺失綜合症,Phelan-McDermid syndrome)的特殊孩子。基因突變的Isla或許整體發展遲緩、或許到九歲十歲仍然不會說話、或許情緒時而不穩定,或許讓與她外出的父母偶爾感到尷尬,但這一切,都無損她的本質——她是神奇妙可畏的創造。
我要稱謝你,因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 ~詩一三九14上[1]
故事始於2016年的冬天,Janice與同是醫生的丈夫Calvin,滿懷喜悅等待著第一個孩子降臨。夫婦二人身體健康,對Janice而言,產檢不過是每個產婦的必經流程,並無太多想法。誰知懷孕五個月時,Janice做完超聲波檢查,竟被告知胎兒的一邊腎有囊腫。此後每次產檢,愈發得知胎兒有更多更嚴重的問題:一邊腎失去功能、心瓣倒流等。羊水不足更導致胎兒發育遲緩。這一切,讓原本滿心期待的Janice,心情變得愈發沉重。
在香港,胎兒若出現嚴重問題,妊娠 24 週內終止懷孕是合法的選擇,但 Janice 並沒有隨波逐流,反而堅定地決定將孩子生下來。她不是沒有過擔憂:她擔心自己無力照顧一個特殊孩子;她擔心將來自己和丈夫老去後,孩子該如何自理;她對神的信心,尚未堅強到能完全無懼前路的難關。只是,她有自己的堅持。
醫生輕描淡寫提出終止懷孕的選項,對Janice來說,卻是一個影響一生的重大決定,她實在難以作出終止懷孕的決定。她和先生都是基督徒,相信生命是神所創造的。Janice對「神的創造奇妙可畏」這句話,更有深刻的體會。面對一個健康正常的嬰兒,人們很容易讚嘆造物的奇妙,但Janice卻在這個被判為「有問題」的胎兒身上,深切領悟到何謂「可畏的創造」——生命本身,就是讓人感到可畏的設計及創造。無論一個人是否符合社會定義的「正常」,都值得被尊重,而非被輕視;因為尊重生命,就是尊重神奇妙可畏的創造。Janice亦從而明白,不要過度放大自身的難處,不要只想著「她」會如何影響自己及家庭。胎兒有「問題」,絕不能用終止生命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夫妻二人商量後,非常確定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棄這條小生命。既然如此,他們做了一個常人難以理解的決定——放棄抽羊水檢驗。
下了決定不代表沒有情緒,從懷孕20週開始,Janice便懷著忐忑不安及沉重的心情等待大女兒誕生。等待的日子裡,夫婦二人無從得知神的心意,也無法預料孩子出生後會面臨怎樣的困境,甚至連孩子能否存活,都是未知之數。當時經醫生診斷,嬰兒出生後極有可能需要接受大型心臟手術,甚至其他治療。這段等待的時光,既漫長又煎熬。但Janice能夠感受到胎兒的跳動,每天可以與丈夫,以及未出世的「她」,這位家庭新成員一起祈禱唱詩及「相處」,Janice認為這都是「賺來的」恩典。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一切都必加給你們。 ~ 太六33
Janice尊重奇妙可畏的創造;神也以恩典及神蹟,回應Janice的信心,讓她不斷看見神的保守及供應。Janice的孩子早產,手術室裡,除了為她進行剖腹生產的醫療團隊,手術室外還有一組兒科醫生隨時待命,準備在必要時為嬰兒進行緊急心臟手術或其他治療。然而,奇蹟發生了 —— 嬰兒出生後經過詳細檢查,心臟竟沒有出現醫生預計的結構問題,不需要做手術。Isla 不僅順利存活,還能和母親同一天出院,只是整體發展依然較為緩慢。
比起同齡的孩子,Isla的進步或許顯得微不足道,始終在緩慢卻穩定地成長;與此同時,Janice 的信心也在一天天積累,Janice並非「信心達人」,Isla的狀況時時變化,她的信心也只能應付當日的難處。從尋找合適的傭人、為孩子挑選學校、尋找治療師、到搬遷新居,甚至是生活中瑣碎的小事,每一次面對難題,Janice 都會將自己的需要帶到禱告中,交託給神。而神也垂聽了她大大小小的祈禱,成為她最堅強的安慰與鼓勵。
除了丈夫的支持,Janice的導師也教導她接納自己的情緒——接納那份「失去一個『正常』孩子」的失落感。在一個罕見病的群組中,她還受到一位家長的激勵及啟發,發現原來一個有特殊兒童的家庭,也可以像「正常」家庭一樣,歡喜快樂地一起去「飲茶」,特殊孩子的兄弟姊妹,也會甘心情願地幫忙照顧。Janice徹底明白一個家庭最重要的核心,是愛與關係;這些寶貴的東西,從來不會因為家中有一位特殊孩子而消失。
有愛的關係沒有因為特殊的Isla而消失,Janice和丈夫,Isla和二女兒Elise,經常一起出外遊玩。在愛中成長的Elise不僅愛心、性格大方,還格外細膩敏感,她從不嫌棄姐姐,反而疼愛著姐姐。若有人不理解Isla的行為,覺得她「古怪」,年幼的Elise已經懂得維護姐姐,告訴其他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別需要。」
Isla不僅有疼愛她的父母及妹妹,她所需要的人和物,神都會在適當的時間,把它們帶到Janice面前。例如當Janice尋找特殊學校的時候,她家附近剛好新建了一座幼兒特殊中心;因為該區人口較少,Isla很順利就讀了。後來Janice搬家,考慮到孩子行動不便,需要找治療師,剛巧又讓她認識到一位住鄰近的治療師。Janice從中體會到當人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一切所需的,神都必會供應。她也常常和丈夫說:「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試驗我,知道我的意念 ~詩一三九23下
從懷孕到養育Isla這段旅程,不僅讓Janice對神的信心不斷增長,更讓她生命中最軟弱的部分,經歷了神破碎及陶造。Janice 的人生從小到大可謂一帆風順,讀書、工作、婚姻,從未遭遇過太大的波折。這讓她一度以為,自己能夠掌控一切,能夠規劃好人生的每一步,但 Isla 的到來,徹底打破了她的「掌控感」,讓她深深體會到不確定性帶來的焦慮,她這才驚覺,所謂的「掌控」不過是一種假象——即便 Isla 就在她的腹中,與她如此緊密相連,她依然對孩子的處境束手無策。正是在這樣的無力感中,Janice 看見了自己的渺小;也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她學會了放下自己,放下想要操控一切的執念,學會了謙卑,開始與神一同經歷人生的種種未知,並且相信:神比她更懂得如何照顧她的女兒。
曾經的 Janice,是一個缺乏耐心、同理心不足的人。身邊的朋友跟她說,Isla 的來臨,是因為神看得起她,揀選了她來承擔這份使命。Janice認同朋友這番話,對此,她在神面前深深俯伏——她知道,神正是在她最軟弱的地方動了「手術」,讓她得以被徹底改變。從前的她,凡事講求效率,總是急於解決問題,從未想過要為特殊孩子多花時間;如今,身為母親的她,面對來求診的患者和家屬,變得格外有耐心,也更願意傾聽和關心他們的處境。
Isla不僅讓Janice變得更有耐性、更為謙卑,更讓她反思何謂「正常」。她發現,這個世界習慣給人貼上各式標籤,標籤一個人「正常」或「不正常」,標籤一個人「成功」或「失敗」,甚至認為只有安靜坐好的孩子,才算得上「乖學生」。直到後來,她才猛然醒悟:其實在神的眼中,沒有人是完美無缺的,每個人都有不同性質的軟弱與不足;但與此同時,每一個生命又都是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
當Janice領悟到這一點後,她的教育理念也徹底改變了。且不說她的大女兒Isla無法贏在起跑線,就連二女兒 Elise,Janice 也從未要求她必須爭強好勝、領先他人。她和丈夫從來不會為女兒們規劃好人生的每一條路,而是選擇賦予她們一項更重要的能力 —— 不是學術上的成就,而是經營關係的能力,以及處理自身情緒的能力。
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深深知道的。 ~詩一三九14下
Janice始終相信,父母若能在孩子年幼時,用正確的方式教養引導,孩子各方面的發展必將終身受益。為了從根源上學習科學的育兒方法,她專程修讀了澳洲墨爾本大學的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 EQ)課程。這是一套專為家長設計的課程,全課共六堂,每一堂聚焦一種情緒,透過情境模擬與角色扮演,引導家長學習用讚美與鼓勵代替責罵與懲罰,並將課堂所學運用於家庭生活中,幫助孩子學會表達情緒、管理情緒。Janice 不僅自己身體力行,更會教授其他家長這套課程。令人驚喜的是,這套課程不僅改善了親子關係,就連手足關係與夫妻關係,也在實踐後變得更加和諧。
從學習做家長,到幫助他人做家長—— 這是 Janice 從未預料過的人生。而她更未曾想過的是,自己這段充滿艱辛與淚水的親身經歷,竟會成為他人的幫助。Janice 願意與那些同樣懷有特殊胎兒的母親傾談,比起那些說著「想當然」的勸解者,Janice 坦然分享自己的處境與心路歷程,理直氣壯地鼓勵她們:請珍惜孩子的生命。生命影響生命,在神的帶領下,與 Janice 深談過的母親,最終都選擇了生下孩子。Janice 相信,神賜予她這段經歷,必有祂美好的旨意。回望走過的路,她深深明白,這是一份很大的祝福。
我未成形的身體,你的眼睛早已看見 ~詩一三九16上
按社會的標準,Isla的發展的確比同齡人遲緩,是別人口中的「特殊孩子」,但她其實是神創造的「單純的喜樂」。儘管她迄今還未能說話,她卻會以純真的笑臉,用力的擁抱歡迎Janice及Calvin回家——一個深深的擁抱,便足以一洗Janice及Calvin一天忙碌後的疲累或壞心情。
「媽咪。」相信這一聲「媽咪」,不會只在Janice的夢境出現,終有一天,Janice一定能親耳聽見,健康快樂的Isla,清晰地喊出那聲她期盼已久的「媽咪」。
[1] 所有經文均引自《新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