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說人人都是記者時,傳統記者、網媒記者及公民記者到底有沒有分別?報業的營運愈來愈艱難,它們究竟有何出路?《媒體解碼:時事背後》集結香港五大資深傳媒人蘇鑰機、陳韜文、李立峯、楊志剛及陳智傑的文章,為大家解讀正在發生的媒體事件、現象。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以豐富的插圖為大家介紹《媒體解碼》的第一部份——性質功能。關心香港傳媒的朋友,值得一看這短片。
作個負責任的網絡記者
上星期初七一遊行,不少市民上街表達不同訴求,但不要以為事件就這樣完結,討論仍然在網上持續。現時社交網站及討論區的方便,讓市民可把自己所看所思,分享給朋友和公眾,就如記者般現場報道、攝影,甚至加上個人評論。所以,不少大眾傳媒未能觸及的情景,往往在社交網站能夠略窺一二。例如在網上可以看到警察如何在水馬陣的空隙向市民使用威力加強版的胡椒噴霧,也看到有警察留言指出議員遞信的狡猾,亦看到遊行過後的街道堆滿垃圾。
當這些圖片或留言被廣泛流傳時,有時更能得到有關方面的回應,讓大眾對事件有一個更全面的認知。
其實縱然立場不同,大家亦可藉此進行理性對話本是好事。但當有些人抱著非友即敵的心態,對提出相反意見的人進行謾罵,淪為情緒發洩的話,那就十分可惜。
另外,現時流行網上改圖,對事件進行調侃、嘲諷。
例如遊行當晚,網上就流傳了一份報紙的頭版版面,標題表達40萬人由維園出發觀看煙花。由於該版面製作認真,故有不少人誤以為這是真的,便在社交網站「分享」給其他朋友,並表示對該報的不滿。在第二天的早上,大家當然會明白原來這只是一則惡搞圖。
究竟改圖者希望進行嘲諷或誤導,確實沒有辦法考究。相信轉載者亦是抱著一顆熱心,甚或變成網絡記者,希望對不公義的事表態。然而作為記者,是有責任查證消息來源,確保消息準確的。當然網民未必需要致電報館求證,但他們只要簡單於有關報章的網站搜尋一下,也會得悉並無相關報道出現。當我們希望尋求社會公義,真相的尋求也是公義的一部分。讓我們也遵守記者的基本操守,即使內容並非出自轉載者,卻仍需盡力確保消息真確及避免誤導。
成報2012/07/12
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
好書推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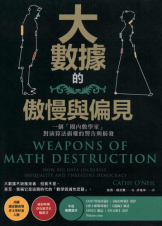
《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一個「圈內數學家」對演算法霸權的警告與揭發》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作者:凱西.歐尼爾(Cathy O’Neil)
譯者:許瑞宋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大寫出版
出版年份:2019年
《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的作者從小熱愛數學,其後取得數學哲學博士學位,曾在大型對沖基金公司擔任量化分析師。作者一度認為數字是公平及客觀的,但隨著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引發經濟崩潰,這信念便瓦解,她描述自己「上了可怕的一課,了解到數學可以如何暗中為害、毀滅世界。」大家都相信程式設計師和統計學家的數學分析,卻很少人質疑統計系統如何運作,它們又是否公平公正。數學——其實可以成為毀滅性武器。
作者走訪了中小學、大學、法院、職場、投票站,為大家揭示所謂客觀的評估其實一點也不客觀。例如在教育方面,美國政府以學生的分數來釐定老師的質素,但作者指出數字並不能說明一切,一位有心力有能力的好老師也可以敗在評分系統上。老師的表現雖然有可能影響學生的成績,但影響學生成績的因素還有許多,包括家庭問題、經濟壓力或個人形象。單單透過演算法歸納人的行為、表現及潛力,並非容易的事情。作者更提到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師,有一年被紐約公立學校增值模型給了六分,第二年卻有96分,兩年來,這位老師都一如既往的盡力。如果不是這位老師的合約是終身制,這位好老師早在只得六分的那年被辭退了。另一位優秀的老師由於她的合約不是終身制,即使她得到校方及學生家長的讚賞,卻因為被增值模型打了一個奇差的分數,而要被迫要離開任職的公立學校。校方願意推薦這位傑出的老師到另一個富裕社區的學校任教。作者諷刺的說:「拜一個非常可疑的模型所賜,貧窮社區的學校失去了一名好老師,富裕社區一間不會根據學生的分數開除教師的學校,則得到了一名好老師。」
由於美國大眾極度「擁護」數字,美國的大學也受到影響。自從《美國新聞》在1988年公佈了第一份仰賴數據的大學排名,當中的排名變成了一種國家標準,大學都想被加分,以致本來的特色都不再重要,反而致力於改進由報社所制定出來的15項準則,這無疑讓教育制度走進一個僵化的模型。有些大學為了推高學校的排名而出錢讓學生重考SAT考試(由美國大學理事會提供的考試);有些直接捏造數據;有些選擇建設豪華的宿舍和健身房。這些費用當然會轉嫁到學生身上。1985年至2013年,美國高等教育成本增加超過500%,學生的借貸也變得愈來愈沉重。
讓人人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是好事,但在美國,有很多「文憑工廠」,目標精準地鎖定為比較容易上當的清貧人士。很多人都在網絡留下足印,一經分析,富人或窮人,以及他們的喜好或需要很容易被劃分出來,精準廣告會出現在不同階層人士的眼前。「文憑工廠」的廣告會說服生活艱苦的人,文憑可以改變他們的生活,可惜的是這些文憑得不到社會承認,入讀大學而來的借貸只會令窮人的生活百上加斤。
數據化時代,亦代表著人人被監視,無所遁形的時代。美國充斥著不少收集市民資訊的公司,以供其他人付費查閱:如Experian、Acxiom、RealPage等,問題是它們所提供的資料不一定精準。不準確或未及時更新的資料可能剝削了居民應有的權利,有位女士便是其中的受害人,她申請老人院時被拒,事緣是RealPage在網上顯示了她的被捕記錄,事實是她的確曾被捕,但卻沒有留下案底,該項記錄亦早已從政府的資料庫中被刪除了。作者指出這些數據公司只管收集市民的資訊,卻不願花時間更新他們的資料,影響了不少人的名譽或權益。
工作方面,為了找出有創意、有智慧和魄力的人才,Gild這類人力資源公司不單會分析員工的履歷表,還會留意他們在網絡上曾否跟相關人才作交流,看看他們是否該領域的活躍人才。作者認為此法並不周全,雖然未至於成為數學毀滅性武器,但隨著數據世界持續地擴張,僱主如何解讀潛在員工在網上發放的生活動態,值得大家留心。另外,作者建議在美國找工作的人,最好不要拖欠信用卡賬單,因為有調查顯示,接近一半的美國僱主在選擇應徵者時,會檢視其信用報告。有時候,拖欠債務可能是事出無奈或一時疏忽,並不能完全反映員工的責任感出了問題,只是當中原因未能在大數據中顯示出來。
作者並非打算推翻統計工具及數據,她只是想喚起大眾的警覺性,知道它們如何對社會造成不公,特別讓低下階層的人成為被追擊的對象,她提出「大數據模型將某種歷史狀態寫進程式裡。它們並不創造未來。創造未來需要『道德想像力』(moral imagination),而那是人類才有的。我們必須明確地將比較好的價值觀寫進演算法,創造出在道德上聽從我們領導的大數據模型。有時候這意味著我們必須重視公平甚於利潤。」
這本書讓讀者明白大數據並不如大家想像的那麼客觀或中性,作者邀請大家多作思考如何善用手中的利劍,才可以讓它們為人類服務,而不是反過來讓它們掌控人類。
與青少年在手機文化中同行
在網絡時代的今天,手機與我們可以說「密不可分」、「形影不離」!隨著智能手機的功能及應用愈來愈廣泛,由與人溝通、處理工作事務,至上社交網站、即時通訊、網購、找資料、找地點、煲劇、看新聞、聽音樂、玩遊戲…甚至起床或提示吃藥的鬧鐘,都設定在手機應用程式內。人們已視手機為私人助理、解悶良伴,以及接觸世界的主要溝通工具。從小生長在網絡時代的青少年,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之下,也成為「手機一族」,甚至出現令人擔憂的使用過度或失控情況。
文﹕郭卓靈 (明光社項目主任)
編輯﹕謝芳
利用手機等科技於學習
「在學校,我們會利用教學管理系統、流動電腦裝置及即時通訊等工具來教學、收發及管理功課,亦會使用網絡與學生討論功課。」崇真書院任教的胡文安主任認為,善用科技可以使學生管理自己的功課及溫習更有條理,亦容易讓老師和學生自己有系統地跟進學習成績及進度。
作為老師及家長的他,又是如何看青少年使用手機的情況?他說,在學習過程無可避免會用到手機,但是有限度的:「只是記錄功課、改正,並寄出給老師,就算討論功課也不會花太多時間。」作為家長,他認為可先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並與子女定好使用手機的規則:「做功課時如要使用手機,是容許的;但使用完即要繼續專注於功課中,完成所有功課後,才能『玩手機』和有時間的節制。」
家長的責任十分重要
胡老師說,曾遇過不少家長問如何令子女不再沉迷「玩手機」。「家長的責任十分重要,如家長與子女的關係在小學階段十分重要,家長應多花時間陪伴子女,並要限制他們『玩手機』的時間,不要讓『玩手機』成為子女的習慣。」他亦認為不要以手機成為小孩子的「保母」:「每當小孩子哭,不少家長就以手機安撫他們,這種做法一定會縱容小孩子養成玩手機的習慣。當他們到中學,若養成牢固的習慣,就難以改變,也會抗拒全然聽從父母的教導。」的確,管教孩子的權責在父母手中,家長才是青少年的榜樣,如果父母日常都沉迷於玩手機,子女一切都看在眼裡時,必然會有樣學樣。
青少年﹕手機有影響作息與成績
分別就讀同校的女學生Bernice和Fish,兩人都承認手機影響了自己的作息及成績,曾想自控,減少用手機的時間,無奈卻難以控制。就讀中三的Bernice說:「當收到訊息時,手機一旦被拿在手,就不想放下…會一直看一直看。雖然明白沉迷手機會減少溫習的時間,但它的吸引力彷彿如一個呼喚,使人不自覺地用不停,一看到有訊息就會立即拿起來看。」「有沒有改善方法?」她想了想,道:「當我畫畫、寫字或練習樂器時,會刻意把電話螢光幕向下放置,那就不會再看見訊息。」她說這方法可讓自己安靜下來。
而中五學生Fish亦表示,在上學的日子,放學後偶而會在whatsapp和朋友傾談或上網玩玩遊戲等,但當要溫習及做功課時,她可以不看手機,讓自己安靜地做功課。
手機與家庭關係
問到有關手機有否影響家庭關係時,Bernice及Fish都表示有點影響,「有時大家都埋首於手機中,未必會交談。」Fish表示當回到家時,有時會見家人在「煲劇」,自己不便打擾便會回房間做功課,大家都習慣沒有甚麼交流。而Bernice亦指自己的父母回到家有時也會埋首手機,去處理工作或了解市場情況,但大家在吃飯或家庭聚會時都會放下手機,十分珍惜溝通相聚的時間。
胡老師坦言自己在社交媒體中,加入成為子女的「Friend(朋友)」,藉以看看子女在網上的分享,以了解他們的想法,同時也可鼓勵孩子建立自己的興趣,那麼,孩子就不容易單單埋首手機。「可能很多青少年未必喜歡加家長做『Friend』,但父母日常的關心時間不能減少。」
「手機文化對青少年影響調查報告」
筆者參與了一個由多間教育、宗教、家長教師會及社會服務團體組成的「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成為聯席的成員,並於本年四月二日向公眾發佈「手機文化對青少年影響調查報告」,內容反映了近一千位青少年使用手機的情況。當我們仔細分析報告,就會發現和上述學生及老師所分享的情況十分相似。
學生使用手機時間長,部份稱控制不了
從報告發現,有接近三成二的受訪青少年每天使用智能手機約三至四小時,亦有接近四份一的受訪者每天使用手機時間約五至六小時或更多;另外,有超過四成的受訪青少年只能間中控制、有時或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使用手機的時間;亦有分別三成及兩成半的學生認為使用手機會影響他們的作息時間及成績。
父母同樣愛玩手機,減少了對子女的關心
另外,該調查亦顯示有超過三成的青少年認為父母因為使用手機而減少了關心自己。根據這份問卷,有超過七成學生在問卷中向父母表達了自己的心聲,當中有不少是希望父母可以放下手機,多和子女溝通;也有表示願意與父母一起玩手機遊戲;亦有學生表示不想父母誤會自己用智能手機是「玩手機」,而是用於學習、閱讀或與同學溝通。
青少年接收新聞資訊與保護私隱
問卷調查的內容亦有觸及到青少年接收新聞資訊的方式及保護自己的私隱,結果發現青少年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不會主動進入新聞網站或網絡媒體去閱讀新聞,並發現他們未必能辨別到甚麼是新聞網站或網媒,可能會錯誤將一些非新聞的內容當作事實來繼續發放。而保護自己方面,受訪者中有超過三成六的青少年於被訪時的三個月內,曾一次或多次與陌生人在社交媒體或即時通訊應用程式中「傾談」,亦有接近半成的青少年曾三次或以上與陌生人出街玩,情況令人擔心。
一點建議
在問卷中,也發現青少年表達自己愈來愈受手機影響及牽制時,他們大可以尋找協助或同行者,互相提點及定下目標,逐步減少使用的時間;與友人一起建立均衡的興趣或計劃外出活動,令自己不會常常因過分空閒或者獨自一人,而又沉醉在手機世界。
而從青少年的角度看,父母會因使用手機而忽略對子女的關心,實在值得大家關注。事實上,青少年每日使用手機的時間不少,能夠騰出空間與父母溝通已十分有限,如父母自己都機不離手,親子時間更見稀少。因此,我們建議父母以身作則,放下手機,珍惜子女相處的時間,多與子女傾談,製造互相溝通的時刻。
最後,我們亦建議應增強保護私隱及傳媒素養的教育,以一些已發生的事件作為討論的開始,使青少年了解如何保護自己,不應於網上與陌生人交談及外出,以免遭到危險。並且讓他們學習接收網上資訊,主動了解時事,同時亦要小心,不應任意發佈可能傷害到別人或非事實的資訊。
(特別鳴謝崇真書院的老師及學生接受訪問。)
談天說道,明報,2017年4月19日
網媒影響力不容小覷
網絡發展已進入「可讀可寫可執行」的Web3.0時代,新聞業的生態被徹底改變。人們的閱讀習慣已不一樣,對資訊的需求亦愈來愈快,令一批網媒短時間內崛起。它們不但為網民提供了許多新聞資訊,也同時令不少紙媒感到壓力,有些合併出版,甚至停刊。為更了解本地網媒的發展與運作、優點、問題及如何閱讀他們的資訊,明光社舉行了一次傳媒教師課程,並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系主任李月蓮博士到來講解,以下是李博士在課程中的一些要點。
網媒報道手法 新聞業界並不支持
「傳媒學生現在要學的東西很豐富,不只是寫作及攝影,而且亦要懂得把故事整理及上載至社交網絡和寫手機應用程式。」李博士又表示,因著網上成立新聞網站的成本很低,網民人數亦多,所以網媒有很大發展空間。大部份香港網媒規模都不大,當中有不少都會用到策展(Curation)的方式,即收集資訊,然後再整理、改寫及精簡,之後再展現給觀眾,外地網媒Huffington Post就是一個成功例子,香港也有部份網媒仿效它的做法。
不過李博士卻提到,其實新聞界並不喜歡「策展」這種抄襲模式:「將新聞改頭換面來刊登,在法津上是難以處理,因為新聞不能有版權。雖然報道可能會列上資料來源,但人們已看了這新聞,又哪有興趣再到長篇的出處去細閱?」
小心閱讀網媒 時刻分辨資訊
由於大多數香港網媒政治立場清晰,有部份更會容許公民記者、博客及學生投稿,提供平台讓市民發聲,因而在社會事件及政治議題上提高了參與度。但亦因著點擊率主導社交網絡資訊的呈現頻率,點擊率愈高該資訊出現得愈密,所以她認為就算是受歡迎的網媒,也不代表公信力高。[1]
另外,她亦關注各網媒趕著刊登「即時新聞」、「即時評論」時,並沒有查證內容就上載。因著網上文化對資訊的準確性並非十分嚴謹,網媒亦未必有足夠人手去查證資料,甚至會因著既有政治立場,在報道上缺乏客觀性,意見及事實可能會混在一起。
所以,李博士提醒我們,在閱讀網媒時要留意新聞來源,了解新聞機構的背景、立場及資金來源。並且要懂得區分內容是議題性或只是非議題性的趣聞,也要分辨那是作者的意見還是是事實,並留意比較報道所列的事實與資料是否完整。
[1] 蘇鑰機,「香港傳媒公信力又見新低」,《明報》,2016年9月8日,網址: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908/s00012/1473270958100
樂見原味新聞歸位

(網上截圖)
近幾年,很多人質疑新聞的內容譁眾取寵,煽情造作,偏頗失實。《眾新聞》走出來說他們要「傳承專業新聞精神,回歸新聞初心,為公眾利益、為公眾服務」。那麼,甚麼是原來的新聞初心呢?我嘗試用一個簡單的方法,想像一下如果相同的新聞材料,放到其他報館手上會怎樣處理。
例如處理行政長官梁振英的UGL事件,記者要做的其實就是搜查背景資料,將從搜查中發現的不妥「還原」為問題,之後告訴讀者:我們發現這裡有問題。今日傳媒首先願意大費周章去做查證,閱讀數以百頁甚至千頁的文件,已經甚少,甚至即使收到其他傳媒的報道,自己也未必會重閱文件,只需草草說「引述XX報章報道」,彷彿文責就不用自負,幾千字「炒台」的作品一下子就完成,記者根本就只是抄寫員。
我們也留意到,整份報道建基於不同的文件,沒有一個消息來自「消息人士」。這種純粹搜集資料就得來的新聞,其實以前常常出現,用清楚的文件去提出合理的質問,本來是新聞日常,可今日的新聞材料,大都是由「消息人士」提供,如此口買口賣「口水稿」(還要不具名),如何能成為有公信力的材料?消息人士各有盤算,記者寫的究竟是這些消息人士的想法、意見,還是他真的知道的事情?如果連第一步也分不清做不到,就隨意下筆,最後這種文章的可信力當然薄過紙了。
眾新聞也沒有避開文件中未能解開的謎團,甚至不怕文件又多又煩,寧願公開慢慢將之拆開解釋。文章中只列出事實,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包括連他查不到但仍然認為是關鍵的部份,也誠實地不知道也就說不知道,不會視而不見。寫的時候也不用譁眾取寵的標題,只列出基本事實。另外,文章會詳列他們究竟曾向多少個機構求證和要求回應,以及他們回應內容。(他們甚至每天都去求證,每天都要求回應,利用他們的版面有無限空間的優勢,每天跟進他們是否願意回應,這態度令人欣賞。)
隨後就是邀請各相關的人回應。如此新聞報道手法,用事實說話,並以所謂的「一分鐘懶人包」呈現,「懶人包」其實就是一個精美的時序表。如果這種材料放在主流傳媒,就一定加幾句「梁振英XXX」;如果是一般的網媒,或許就二話不說,將自己的想法,甚至是個人的政治議程放上去了。這種無添加的做法,相信會令看慣現時新聞的人,感到十分不習慣。
又有另一則相關新聞,亦是談到關於梁振英利益申報的情報,不過記者卻用另一種方法:電郵到美國白宮去查詢總統的利益申報,然後將之與香港的特首對比。文章同樣少有評論香港的利益申報制度,只說美國總統提供的資料,內容比香港特首申報的更詳細,之後記者就是介紹兩地的利益申報制度。或者你會質疑,這種新聞究竟有沒有「新」聞,還是只是我們已有的知識?但其實她多了一份查證的功夫,傳媒機構真的找記者去問及等回應。整件事的之所以能成,也是建基於對方的回應。尋常的人和事在有觸角的記者手上,亦有機會發現其新聞價值。
當然,我們了解到《眾新聞》其實人手很少,所以新聞數量根本不多,大部份的文章仍然是評論,但難得地他們在採訪和評論劃下很清晰的界線,編採和評論很難得地分家。新聞就是新聞,將之還原只報道事實,評論就另外從看到的事實用不同角度分析。習慣看先有立場而寫的新聞,我們看完雖然彷彿知道整件事的一切,但原來卻因為要方便預設的立場,新聞不會寫一些對他們預設立場不利的部份。由於《眾新聞》將事件盡量還原,最後你要做的,可能反而要多看幾篇文,才能跟得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但同時你得到的訊息,相對更整全。
我們天天看的報章新聞,就像即食麵,好像很豐富,很多味道,但誰都知道,這和偏食沒有分別。要生存,我們需要的是清水。但願多點清水,能使我們早就失去的味覺漸漸回復過來,以致我們能更好去閱讀新聞。不過,請謹記,濁世清泉,價值不菲,但願有人去珍惜。
獨立媒體,2017年1月5日
網媒記者爭取採訪權
一向本地的網媒記者、學生媒體及公民記者都不被香港政府承認,也不會被邀請採訪參與記者會,亦不能收到政府發出的新聞稿和使用政府新聞系統。於本年二月新界東立法會補選投票日,一眾網媒亦被拒以記者身份進入新聞中心採訪。為此,部份網媒發出了聯署,記者協會亦向政府發出聲明,促政府立即開放網媒及公民記者的採訪權,承認具公信力的網媒地位。[1][2]
我們已進入網絡時代,新聞除了傳統的報章及電視電台外,市民大眾接觸新聞的渠道亦包括影響力漸強的網絡媒體,參與網絡新聞的工作者,無論是否全職,又或是公民記者、學生記者… 都認該被尊重。否則新聞自由及資訊的流通可能會被影響。
當然,由於新聞業是一種專業,不能人人都可以做者,為保持質素,新聞工作者要維持其應有的操守、遵守記者守則,如:不能扭曲事實、不侵擾當事人或作出偏頗的報道。盼望政府早日面對媒體的發展,參考外地的做法,與世界接軌。
記者是不甘寂寞還是被逼上梁山?
於雨傘運動期間,市民透過新舊媒體得知最新資訊,加上公民記者湧現,記者報道的中立性屢受質疑。為了探討此現象,明光社及香港傳媒教育協會於2015年1月16日假中聖書院禮堂合辦「雨傘運動的媒體操守」座談會,當天約有30多人出席。
有人指記者在報道雨傘運動的手法是「不甘寂寞」——很想達個人政見;也有人認為記者是被人「逼上梁山」——因為稿件被上司大幅度修改而在新媒體另闢表達空間。座談會嘉賓除了探討此情況,同時也討論了傳媒立場與公信力的關係。
至於在新舊媒體角色一事上,嘉賓也同意公民記者其實不是專業記者,但能與主流傳媒作出互補。而要解決現時媒體出現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就要解決社會的問題。」
蔡志森:記者需學習成為旁觀者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首先以前記者身份,提出關於現時傳媒有否規範的疑問。他認為現時一些記者不甘寂寞,「想把自己理念及看法,透過報道說出來。」此外,他亦認為雨傘運動看到不同世代的撕裂,包括兩代如何看記者的角色。「參與社會行動的記者以往不會用記者身份,但現在卻高調參加。」
他更質疑記者應否在現場隨時變身,使用記者證作為「免死金牌」。對於先前有報道指有團體派出200名成員於運動化身成為公民記者,蔡亦質疑是否人數愈多就愈好,「還是愈多愈混亂」。他建議記者要學習成為球證,在旁觀看,而不是夾在衝突中間,甚至像參與者投入於運動中。
岑倚蘭:佩服記者行家無懼風雨採訪
香港記者協會(下稱記協)主席岑倚蘭(岑倚)佩服很多行家於79日無懼風雨及挑戰。她指出運動期間最少有32名記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甚至「記協亦曾被人衝上門口抗議。」此外,有記者當時被上司要求拍攝金鐘混亂場面,可是現場根本並不混亂,他更拍得佔領者開路讓救護車駛入現場。他將此情況撰寫出來,但標題卻被改成佔領者妨礙救護車前行。岑倚蘭指出,「當如實報道不被刊登時,唯有下班後去成為網絡媒體義工,去平衡心理。」
另外,她指很難定義公民記者是否記者,但不認同「穿著印有Press字樣的背心去充當佔領運動的義工」。她並不否認公民記者的重要性,但這些報道及資料如何使用,就是媒體要小心處理的問題。在承認記者身份及發記者證方面,記協背負很大責任,因記協記者證「可申請國際記者證,警方亦認可」,故要非常小心。
陳珏明:我就是被逼上梁山的一位
852郵報記者陳珏明(珏明)於雨傘運動期間採訪時,提醒自己不要與警察「開火」,可是現實卻是「偏偏不斷開火」。
他曾被無理拒絕進入封鎖線後採訪,並被警察帶離現場。有指現時記者不甘寂寞,他指「我更覺得是被逼上梁山」。他指記者的報道與事實不符或被扭曲,唯有選擇在互聯網上發表。
他坦言自己十分支持這場運動,但他為了保持中立性,故堅持不掛上黃絲帶,甚至下班也不會帶,「就是為了精確的報道」。他會提醒同事「不要覺得喊口號沒問題」,因為這會令人覺得有失中立性。他坦言現時記者要成為球證愈來愈難,「因現場不是對等的比賽,警察比市民有更大權力,很難稱為中立比賽。」
蘇鑰機:新媒體影響漸大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蘇鑰機教授透過其研究,指出於一般情況下,有接近一半受訪者仍是最常收看免費電視新聞,其次是閱讀收費報章。而愈年輕及教育程度愈高的受訪者,使用社交媒體會愈多。蘇指出「社交媒體對雨傘運動的參與者很重要」,他比較蘋果日報、明報及香港獨立媒體網,發現於雨傘運動前後,明報facebook專頁的被like數目升逾十倍。
而這段期間透過facebook發放的報道,有九成是與佔領運動有關。蘇認為傳統媒體仍是很重要,但社交媒體能夠讓人「知道、分享,更可以留言」,人的參與及表達感較強,能與傳統媒體互補。
傳媒中立的迷思
至於在傳媒是否需要中立一事上,岑倚蘭指於運動期間有人提議記者杯葛某團體的活動,「隱含對這種為中立而中立的傳媒老闆抗議」。然而她卻認為持多元化意見的傳媒,可以讓市民有更多選擇。
珏明則認為「對暴力也是有立場,有價值判斷,但不會覺得有問題。」他指記者要呈現真相予市民知道,即使現場直播,也可以是偏頗。蔡志森則認為傳媒可以有立場,但意見應於社論內發表,不應混入報道中。「我們期望警察專業,為何不能期望記者也是專業?」
有台下觀眾指傳媒使用社交媒體快速發放消息,岑倚蘭觀察到不少記者於自己社交網站掛上黃絲帶,表達自己的立場,然而「外國記者是有手冊嚴格限制政治立場表達」,但香港記者則不斷表態,甚至穿著記者背心成為雨傘運動義工,是會影響公信力的。
記者的使命何在?
有觀眾問及記者使命,岑倚蘭指上一代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對現時媒體偏頗甚至「自我閹割」感到失望。蘇鑰機則指於學理上記者有兩大角色,其一是提倡中立,另一種是參與性較高,提倡公義。蘇認為兩種記者的比例與社會情況有關,參與式記者較多,代表社會有問題。「要解決記者出現的問題,就要解決社會的問題。」
縱然雨傘運動已告落幕,但由之引起的新舊媒體的發展與爭議將仍然繼續。這個座談會只是一個開始,我們冀盼日後能再進深探討此課題。
在世界中心自拍—網絡自我分享
當你走到世界的中心,山嶺的高峰時,你會第一時間做甚麼?當然是自拍,然後放在社交網絡分享。為了令相片更易「呃like」,就算要站在更危險的邊緣,用上更多時間修圖也在所不惜。但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山上的風景,你又看到多少?
潮流最近興上網寫日記拍照分享?黃子華早於2009年已諷刺這些人把自己看成偉人一樣,把所有事寫成「傳記」,放上網讓人觀看。「若不是,你如何解釋你會給早餐餐蛋麵拍照,然後放上網給全世界觀看?」[1] 而有賴於facebook動態時報(Timeline)相助,大家可以按年份瀏覽有關朋友的分享,把「傳奇」提升至更高層次。
自拍自戀與自我形象
但在分享自我的同時,亦經常出現自我中心,甚至自戀的情況。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研究指,同樣是大學學生,58% 以上的2009年學生比1982年學生有更高的自戀評分。[2]
青少年渴望被認同,但其實所有人亦然,在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中的第二層就是尊重 (Esteem) 的需求。在互聯網發達的年代,青少年有大量機會與同輩交流。透過社交媒體,大家能夠互相了解及互動。有研究指在網上分享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需要被認同,包括建立個人形像、提升自信、獲取尊重和支持。[3] 若要被別人認識及認同,就要不斷分享。故平日的吃喝玩樂也要包括其中,甚至在任何一個地方自拍,也是「呃like」的好方法。2013年「自拍」 (selfie) 一詞成為牛津字典年度詞彙,可見自拍已成為人氣首選。
自拍不但讓自我感到滿足,當自拍照上載到社交網絡,亦提供了與人互動溝通的橋樑,加上文字的輔助,讓觀眾不僅看到生活中的自己,甚至是「內心的我」。[4] 而自拍者停不了的自拍,顯示他們不只希望得到一次性的認同,而是希望不斷得到認同。這種短暫的滿足、甚至虛榮,帶來更多的自拍,填滿慾望的空洞。[5]
「出眾」的相片 讓人看見最美的一面?
若自拍是為了要吸引注意,那麼就要令相片更「出眾」。出眾可以是因為設計更美的構圖,也可以是在特別的場景拍照,更可以是經修飾出來的效果。
愛美是人的天性,盡量讓自己最美的一面留下,其實合情合理。這種挑選式的自我形象建立,就是要讓其他人看到,甚至放大自己的美。所以自拍「高炒」是常識,就是要讓自己的下巴尖尖,眼睛大大;若仍然不滿意的話,修圖軟件就能大派用場。然而,這個更美,更多人like的自己,其實只是一個希望別人看到的自己。想想由此而得到的like,是因為朋友喜歡這個誇大甚至不真實的自己,還是因為閣下卓越的修圖技巧?
至於特別的場景,就是在別人不會自拍的地方自拍。但有否想過拍攝場地的是不是一個合適自拍的地方呢?奧巴馬、卡梅倫及丹麥總理施密特曾經在曼德拉悼念會上自拍而備受批評;[6] 更有美國飛機師在駕駛小型飛機時使用手機發短訊及自拍,導致飛機失事,賠上生命。[7] 本地亦有學生於公開試試場拍照,並把違規罪證放上網。[8] 而「人類總是重複同樣的錯誤」, 2014年底解款車跌錢事件,有人竟然把自己順手牽羊的「錢磚」拍照並上載至facebook炫耀一番。[9] 拍照者渴望成為焦點,卻忘記了應有的禮儀,甚至事件的不當性。
小心自拍成癮
當不斷追求更美的自己,小心可能已成為一種沉溺,有男孩每日自拍200次,期待拍下更好的自己,但因不滿意相片而嘗試自殺。其後他獲救,並被診斷患上身體畸型恐懼症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此症的病癥是過度關注自己的外表,尤其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瑕疵。然而當他放下手機,走在街上,才發現原來途人不會留意自己,他也因此不再常常留意自己的外表。[10]
「爬上高山讓你看到世界,而不是讓世界看到你。」
我們渴望成為特別的一個,故此希望透過網絡分享,獲得更多的認同與讚賞,但倒頭來反而不能再做回真實的自己,還會帶來麻煩。原來全世界就有68億個不同的人,我們也是「同樣地不同」。英文老師David McCullough Jr.於2012年在衛斯理高中 (Wellesley High School)的 畢業禮上向畢業生提醒把握當下,無私才是你可以為自己做最好的事,而並非著眼於自己得到甚麼讚賞。「爬上高山讓你看到世界,而不是讓世界看到你。」。[11]
同樣,網絡讓我們看到世界,不是讓世界看到自己。
-----------------------------------------------------------------------------------
分享事情的方式轉變
過去:面對面口耳相傳
現在:透過手機上傳照片
這世代,太懂得分享了。以前要與別人分享一件事,往往要面對面口耳相傳,但現在只需於按一個鍵便可昭告天下,所以搞笑事特別多。有人扮病請假,在FB打卡(分享行蹤)被人發現原來「詐病」;有人跟女朋友說要加班,豈料朋友將他們到酒吧玩的相片放在FB,最後當然「人贓並獲」,遭女友發現。不少人甚至將自己犯法的事情放在網上,如展示兒童色情圖片,甚至有偷竊、縱火等罪行。上載者以為沒有人知道,最後卻輕易被警方拘捕。可見分享所帶來的所謂方便,有時自食其果。
[1] 黃子華棟篤笑《嘩眾取寵》,2009
[2] John Stein,”Millennials: The ME ME ME Generation”,TIME,20.5.2013
[3] 潘志謙、梁永熾, 『「網世代」在網上發布內容的原因』,香港電台,2010/08/14,網址:http://app3.rthk.hk/mediadigest/media/pdf/pdf_1405312123.pdf
[4] 葉倩如,《我與我的納西瑟斯自我影像作為電腦中介溝通之線索--試以網路相簿自拍照為例》,中華傳播學會,2007 年,網址:http://ccs.nccu.edu.tw/word/HISTORY_PAPER_FILES/689_1.pdf
[5] 黃婉婷,「誰在看我?青少年自拍多重研究」,2012年,網址:http://140.127.82.166/retrieve/14861/114.pdf
[6]“Obama, Cameron, Schmidt take selfie at Mandela memorial”,BBC,10/12/2013,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5322260
[7] 「機師狂自拍 墜機兩死」,《蘋果日報》,2015年2月5日,網址: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50205/19029649
[8] 「考生涉試場拍准考證放fb」,《明報》,2013年410日,網址:http://edu.sina.com.hk/dse/news/98/1/4/132740/1.html
[9] 「執錢唔還犯四罪可判囚」,《東方日報》,2014年12月27日,網址: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41227/00174_001.html
[10] “Selfie addict took TWO HUNDRED a day – and tried to kill himself when he couldn’t take perfect photo”,Mirror,23/3/2014,http://www.mirror.co.uk/news/real-life-stories/selfie-addict-took-two-hu...
[11] ” Commencement speaker blasts students”,The Washington Post,8/6/2012,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answer-sheet/post/commencement-speak...
傳統記者與公民記者的互補
不知道在佔領運動完畢後,大家看新聞的習慣有否改變。在運動期間,大家不難發現縱然報道同一件事,媒體報道內容亦會大不同,有人因此毅然轉台,或罷買某份報章,有人亦因希望更快更廣地得到最新消息,從而瀏覽網絡媒體的報道。
然而就算網上媒體與傳統媒體不同,隨著愈來愈多市民注視往後政局發展,所以仍有很多人瀏覽網媒的專頁。網絡媒體很多時也是由公民記者提供消息,由於公民記者往往身在前線,並且數目眾多,故此能補充傳統媒體忽略的另一面。而這種透過公民自發參與的新聞報道,被稱為參與式新聞。參與式新聞重視由下而上的發佈,發佈者亦同時為接收者,角色平等,故此與一些爭取民主的運動相襯。
雖然不少人也開始看公民記者的報道,但也出現不少質疑的聲音,特別對於他們的報道中立性及公信力。早前亦有報道指不少公民記者在報道時,亦會走到前線成為抗爭者,致他們公信力成疑。這就好像出現一種對立:傳統記者還是公民記者可信,或者比較專業。但話說回頭,正正是因為傳統媒體的立場偏頗,其公信力亦屢受質疑。有說記者曾接受大學新聞系的訓練,但現在不少非新聞系畢業生會選擇成為記者;有說記者可加入記協,遵守記者守則,但有報道卻指只有兩成記者是記協會員,比例不高,亦有不少記者因各種理由不能入會;有說報道新聞是建基於客觀求真的態度,但這看來也未必讓市民信服。那麼,當我們要求公民記者報道要專業的時候,傳統新聞工作者其實也要作好榜樣,不受政治、市場影響而盡力揭示真相。
在這個大是大非的環境,記者也是社會的一份子,也希望揭示真相,伸張正義。在現場看到種種不公的情況,自然希望報道出來,讓社會得知。有指為著公眾利益,報道縱有明顯個人立場也是無可奈何。但實情是如何能夠基於客觀事實作陳述,才是最能讓不分左中右信服的報道。對於公民記者何時工作、何時抗爭的情況,這是公民記者希望作更具說服力的報道時,應該反思的一環。而傳統及公民記者的互補,才能讓市民能夠更易從眾多資訊中,看到事實的更多面向。
《成報》 22/1/2015
在時代的洪流滑浪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簡單兩句說話在雨傘運動引起不少共鳴。香港雖然不是處於甚麼亂世,不過,人心的亂,比治安的亂更令人躁動不安。每當處於一些歷史轉折的關口,面對一些未知的變化,人心總會不安,為政者若未能妥善處理群眾的不安,很容易便會演化成大型的社會運動,甚至騷亂。若個人未能妥善處理自身的不安,便可能感到迷惘,甚至抑鬱。
香港雖然只是中國南方一個小漁港,但在歷史上卻有絕不平凡的地位和經歷。而過去半個世紀,不少香港人都一同經歷著很多不平凡的時代風浪,可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屈指一算,由上世紀60年代因國內文革而起的暴動;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草擬;97回歸;2003年的沙士及七一遊行;以至2014年底的雨傘運動,幾乎每十年我們都會遇上一些席捲全港,無人能置身事外的大時代。
對於喜歡刺激的人,一浪接一浪當然令人興奮,就像高潮迭起的電影一樣引人入勝。但對於心臟虛弱的人來說,經常擔驚受怕實在會吃不消。不過,無論大家是否喜歡,對於無法逃避的事,既來之則安之,應該是最明智的選擇。此外,如何在這些大家都已付出不少心血代價的大時代中不至交白卷,空手而回,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沒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只會不斷重蹈覆轍,成為歷史的笑柄。
本期《燭光網絡》希望透過訪問一些時代的觀察者,由他們在不同時代的觀察,協助我們一起剖析上述不同時代值得總結的經驗,作為個人以至整個社會一起的反思。面對大時代,個人其實十分渺小,能夠成為時勢英雄的畢竟只是極少數,不過,大家想深一層,其實當時代的巨浪打過來,每個人最後都是要自救,其他人是難以相助的,因此,學會觀察及捕捉巨浪的來勢,才不至被浪舌噬。面對大時代的洪流,一起學習如何滑浪吧!
一起走過沙士、七一的日子
2003年是紛擾的一年,香港人歷經非典型肺炎(沙士)一役,接踵而來的是有五十萬人參與的七一遊行。在那年,生命似是特別脆弱,香港人坐困愁城,盼望「光復」的日子。然而,疫情剛過去,香港人因長期受政治民生問題壓得喘不過氣,結果在隨後的七一遊行通通爆發出來。現在回望2003年,我們怎樣走過那段日子?
邢福增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邢院長當時於長洲的建道神學院任教,雖然地理位置上看似遠離「災區」,但是他仍有經歷戴口罩及學校停課的日子。「那時的氣氛確實很灰暗,疫症剛開始時,沒有人確定是由甚麼病菌引起,大家人心惶惶。雖然後來能確定是沙士,但眼見每天感染病菌及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心情自然也十分低落。」
在低氣壓濃罩下,整體香港社會一片愁雲慘霧。基督徒縱然有信仰支持,但也不能倖免。特別在生命危急關頭,面對茫然未知的情況,人有時也會傾向想找出事情的因由。
邢院長憶述當時的基督徒群體也廣泛流傳一些沙士出現的「原因」:「當時曾有流傳,指因為某局長身為基督徒卻為香港求簽,觸怒了上帝,上帝因而利用沙士懲罰香港。然而,這樣卻只是將沙士演繹成人犯罪後的懲罰,亦是把信仰約化成解釋現實的理由。信仰並不是用來解釋現況,而是一份助人面對晦暗不明前景的力量。」
在最壞的境況中,也是讓信仰發揮力量的最好時候。邢院長在疫情稍緩時,於建道神學院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舉行講座,探討疫情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基督教與其他民間宗教對疫情的詮釋有何不同,藉著講座疏理當前的境況。
但早在沙士肆虐期間,信仰透過一位又一位的基督徒展現。謝婉雯醫生是首位殉職的公立醫院醫生,她亦是一位基督徒。在沙士爆發期間,她主動提議調進醫治沙士病人的病房工作;後來因感染沙士而離世。謝醫生的生命本已是一個美好而又實在的見證。
這段時間亦是一個反思生命價值的好時機。「沙士以前,香港人只懂追求物質上的滿足,只想要滿足自己那無窮無盡的慾望,但那時卻是一次的停頓位,讓大家思考是否仍要過這種無止境追逐式的生活。」
疫情剛紓緩下來,便爆發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遊行。香港市民對當時的特區政府早已累積一定怨氣,再加上後來沙士爆發及政府處理手法失當,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因此,雖然那次遊行以反對廿三條立法為號召,但從遊行隊伍各式各樣的訴求中,不難發現市民們其實藉此發泄一直以來積存的怒氣。
今天的香港教會會為著當前的情況表達意見,那在2003年呢?「印象中,除了協進會、基督徒學會及個別宗派,大多數教會並沒有表達意見」或許是剛經過沙士一疫仍在回復元氣,或許是關乎政治的事,教會要與之劃清界線。但無論如何,邢院長認為基督徒有著雙重身份:「基督徒既是天國子民,也是地上的公民;我們天國子民的身份並不削弱地上公民的社會責任,反之亦然。」
若從2003年的經歷面對現在的香港,邢院長寄語大家要持久地追求目標。「沙士的時候,大家從紙醉金迷的生活中覺醒了,意識到生命並不只是追求無止境的渴望。可是這種覺醒很快消失了,至今唯一能長遠改變的,就只有我們洗手的習慣,以及水嚨頭由開關式變成自動感應式了。」
李炳光牧師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前會長
當時還有半年,李炳光牧師便退休了。怎料卻在2003年上半年爆發沙士,普通人若是遇上這情況,或許會暗嘆倒楣,不能安安樂樂完成任期;但李牧師卻看見截然不同的景象,「那是上帝給我的特別挑戰,在那個艱難的時間中讓我參與。這也是神讓我服侍及關懷有需要的人。」
李牧師口中的「有需要的人」,正正就是前線的醫護人員。那時,李牧師正擔任院牧事工的主席。面對著每天不斷攀升的感染及死亡人數,李牧師坦言當時確實愛莫能助,而教會所能做的事又十分有限。縱然如此,教會仍有可以承擔的一份。
「那時,教會與當時仍是主教的陳日君樞機一同舉辦露天祈禱會,為香港禱告。此外,在前線的醫護人員因著職責而不能回家,我們想到可以為他們及其家人安裝遙距鏡頭,讓他們見面,以解相思之苦。當在主日宣佈這項計劃時,弟兄姊妹十分踴躍,僅僅在一天的幾堂崇拜已籌得足夠款項,並在那打素醫院設立有關設備。」
回想那時的氣氛,李牧師記起社會瀰漫著無奈及焦慮。「因為疫情開始時並不知道由哪種病菌引起,所以人心惶惶。」教會那時亦因此而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所有會眾帶著口罩參與崇拜,從講台上望下去,只見大家露出雙眼,但仍感受到大家的不安。至於發聖餐時,亦要改用鉗子分餅。」
李牧師感嘆雖然現今醫學昌明,但人的力量依然微小。面對著突如其來的病菌,人仍然束手無策。然而,在幽谷中,在人的脆弱上,卻使我們不得不謙卑下來:「在沙士期間,雖然不明白當前的境況,也不明白為何會發生這事,但面對著人的渺小,卻體會到神仍是真實的,唯有在祂裡面才有永生的盼望。」
誠如李牧師最喜愛的一首詩所述,面對看似毫無盼望的困境中,神仍在其中,我們仍然有盼望:
「雖然我看不見藍天,我仍相信有藍天;
雖然我見不到陽光,我仍然相信有太陽;
雖然我看不到上帝,但我仍然相信有上帝」
岑倚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
2003年,岑倚蘭(岑倚)是《經濟日報》的副老總。
那屆政府軟弱無能、市民希望她做到的沒有做;反倒推行不得民意的政策,加上經濟低迷,令市民驚覺需要走到街上表達訴求。雖然當年的市民或基督徒對事件有很多意見,然而並沒有出現如今天的撕裂。「今天出現多元的意見,其中一個原因是兩代人看事物的角度不同。昔日走上街頭表達訴求,完成路線後便會分散,回歸生活中;然而,今天的公民社會成熟、公民意識強烈提升,再加上社交媒體的威力,令公民運動的模式有很大的轉變。」
在後佔領時代,上一代人就如明燈,是意見提供者,新一代卻會按自己的取向而選擇方向;上一代人擔心年輕人有生命的傷亡,新一代卻認為他們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去面對一切。政府不能再以舊有的方式面向新一代,正如台灣新一代用選票告訴國民黨他們要懲罰馬英九,香港新一代同樣可以用選票去決定誰人可進入政治體制內,年輕一代相信命運自決。誠然,中國 / 香港政府已失去了香港的新一代。
經歷風雨的岑倚,身處今天的動盪社會,欣賞港人願意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與在宗教價值基礎中建立的普世價值,並在充滿謊言與歪理的社會中讓人分辨是非黑白。同時寄語大家在面對謊言與歪理時不要讓憤怒掩蓋一切,應理性思考並認清需付的代價。
作個負責任的信息發佈者
就近日有關台灣服貿協議爭議的報道,大家是從哪裡看到呢?傳統媒體給讀者的大多只是最新進展,但若果在網上搜尋的話,更可看到現場直播,而你亦順道能找到不少分析。在這個「人人做記者」的年代,不少人都在自己的「地盤」或在網絡媒體上分享。加上智能手機十分普及,要拍照及短片亦十分容易。這批被稱為「公民記者」的人,不再只是被動地接收資訊,而是主動參與及報道,甚至傳統媒體有時都要借助他們的資料作報道。針對台灣的情況而言,由於不少台灣人不太信賴傳統媒體,亦令更多台灣人轉而選擇閱讀「公民記者」的報道。
然而,「公民記者」不少是沒有經過專業的新聞訓練,他們對新聞報道講求的準確性及客觀性,往往未必能拿捏得準。例如不少人看過的「黑箱服貿懶人包」影片,當中提及有關香港2003年簽署CEPA後的情況,而且亦有不少人引用。縱使圖表上的數字正確描述香港經濟狀況的改變,但卻沒有提及其實在2003年前已有下跌趨勢。因此,香港經濟狀況的改變亦是否一定關於簽署CEPA呢?似乎沒有足夠證據。
另外,由於資訊瞬息萬變,就算傳統媒體也有出錯的時候,若「公民記者」的報道出錯本來也可理解。但當一個負責任的媒體發現報道出錯,是會作出修正及道歉的;並且會影響媒體本身的公信力,以及觀眾、讀者對該機構的信任。同理,當公民記者發現自己的報道出錯時也應願意承擔。例如在行政院清場當晚,有人指警察踐踏民眾 (實際上是警察跨過民眾),以及撕下臂章免被投訴。及後被證實純屬誤會,台灣作家九把刀雖不是「公民記者」,但他在分享有關圖片後也負責任地作出道歉。
近來另一個在經常出現的現象,就是很多人未經考究,不分真偽便將一些聳人聽聞的消息或呼籲透過手機轉發,在WhatsApp或facebook的朋友群組間接散播中傷他人、冒名偽造或改頭換面的呼籲,令謠言滿天飛。
因為渴望揭露真相,擺脫傳統媒體的「拘束」,所以不少人想擔當「公民記者」。在這個科技發達的年代,人人也可以輕易透過手機或網絡發佈信息,但一個不願意小心求證,謹慎發佈信息的人根本沒有資格被稱為記者。當我們渴望揭露真相的同時,也要注意必須作個負責任的信息發佈者。
人云不等如我亦要云
網上資訊紛雜,令人難分真假。上周六正值清明時節,就有網民上載一段「無頭鬼公路截車」短片,在片中見有疑似無頭人形物體在「截車」,使人即時難分真假。短片在網絡迅速流傳,後來被網民轉載在不同的社交網站,翌日更有報章報道,記者煞有介事般找來堪輿學家、物理學者分析一番。
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往往可以成為吸引人的焦點,但問題是,我們在面對真假不清的資訊時抱有甚麼心態。網絡資訊的流向往往始於小眾之間,但之後會在不同的社會族群交叉流傳,結果是消息未傳到傳媒之先,就已經以幾何級數般散開。加上現時互聯網科技進步,更加速訊息轉傳。不消幾小時,甚至幾分鐘,一個消息就可以一傳十、十傳百的方式傳開,而且更可以成為全城熱話。當推上報之時,消息甚至已經成了明日黃花。
所以,當傳媒收到這些訊息後,應從兩個向度思考是否報道:
- 資訊是否真確。網民以「有圖有真相」作為評定網上消息真確與否的標準,但如果從新聞的角度,我們對真實的要求相對比較高。一般沒有消息來源或者來源不明的,不應輕易相信,若有懷疑而又未能求證,傳媒甚至不應報道;
- 資訊的重要性,以及對社會的意義。既然有關事件已經在社會廣傳,我們就要問這事情是否值得放在密密麻麻的新聞版上,而整件事又是否反映社會甚麼實況與趨勢。
可惜的是,現在傳媒往往只着重以娛樂化方式包裝新聞,記者既不求證又不求真。傳媒只以花生族的心態找些人來回應故事,以求博得讀者一笑,他們只抱有一種將新聞瑣碎化、娛樂化的態度。更叫人擔心的是這種情況不只發生在「無頭鬼公路截車」這些短片上,更會發生在報道大是大非之中,例如報道政改,新聞角度極像後宮爭寵,報道用字不是「叩頭」就是「扭擰」;甚至有報章天天就畫漫畫,談的都不是政策內容,而是政治八卦。
香港人今日望見傳媒自動投降,同時社會各種良莠不齊的資訊在網上不斷以私人的方式轉傳,甚至有人以網絡作為政治動員的工具。我們除了要分辨資訊真偽,還要檢視自己閱讀資訊的態度,不要被扭曲的閱讀風氣和傳媒文化影響。若你看到或聽到一件值得懷疑的事時,請持守敏銳的心;假若沒有時間去努力查證,尋求真相,那麼一笑置之,千萬別做散播謠言的幫兇,人云不等如我亦要云。
性別,由你話事?
最近,在全球擁有12億使用者的社交網站Facebook在用戶設定上作出了重大變更:在「性別」一欄,除了傳統的男和女,更讓用戶自行選擇多達48種的不同「性別」選項。這些「性別」包括男變女(Trans Female)、性別不確定(Gender Questioning)等。可是這種做法究竟是真的「襟個制」就可以性別「由自己話事」?
這項Facebook設定的改變,有人說是一個重大變革,讓使用者可以跳出傳統性別二元的思考模式,並反思性別其實可以是有其多樣性。不過,這種做法與其說是跳出「傳統二元」的模式,倒不如說是「墮入」酷兒理論的論述框架內。這其實是多麼諷刺的一個事實:當你以為突破了傳統的枷鎖,自以為自己已享有真正的自由時,卻不知道自己其實在不知不覺間被新的枷鎖所束縛。
性別選項跳不出傳統框架
尋求變性的人士,他們在人生中往往經歷了無數艱難時刻,包括自己內心的掙扎、家人關係變差、社會人士的目光,以至因使用過量異性荷爾蒙所帶來的副作用。甚至後來走到接受變性手術的階段,他們身心靈所受到的創傷往往不足為外人道。不過,即使前路多艱苦,這些朋友心中卻只有一個盼望,就是希望在接受變性手術後能有更美好的生活,那怕只是感到多一點的自在。經歷這麼多的苦頭後,他們心底裏都只是希望能成為另一個性別,即是一個男性或一個女性,這始終都沒有跳出傳統性別二元的框架。那麼為何還要製造更多的「性別」呢?
可是,當你誠實地寫你的性別為「性別不一致(Gender Nonconforming)」,是否真的會得到多一點的身份認同?還是會引起其他人(或自己)更多的問題?Facebook在個人資料中表面給你很多「選項」,去建立自己的網上形象,可是值得反思的是,我們的自我形象,真的就只建立在這些「選項」之上嗎?如此,增多了多少「選項」,也只是「增多」了,甚至「選項」也可以複選,但這些「選項」就真的代表了我們生命的價值?
我們只能選擇怎樣面對生命
人生往往充滿無奈和限制。有些事,可以由我們自己話事;有些事,則是我們自己無法改變的。也許這種說法對不少朋友來說顯得有點無情,特別是那些尋求變性的人士,然而這卻是殘酷的現實。變性手術可以改變我們身體的外觀,包括性徵;可是人的生理性別(Sex),XX(女性)或XY(男性)的染色體卻打從我們出生便伴隨我們終老。即使你再不喜歡,這也是你的一部分。你可以透過手術改變性器官,可惜它卻無法像原生的性器官一樣有完整的功能。
我們常常以為自己在為自己做選擇,卻往往不知道有些事是我們無法掌控,我們能選擇的是怎樣面對自己的生命,怎樣面對人生的無奈和限制,在這之中尋找人生的意義。
新聞不是笑話
在這個資訊瞬息萬變的年代,為了避免出現其他傳媒都作出報道,自己的媒體卻「獨甩」的情況,媒體每每見到有新聞出現,未經求證就報道出來。而後來當大家發現錯誤,也只會低調更正,甚至直截了當地刪除網站報道,實在未能有效令讀者明白真相。
在這個「人人做記者」的年代,一些報道隨時經過幾手評論及修飾而變得面目全非。尤其一些誇張得超乎常理的報道,若果該事件連時間、地點及人物也不明確,消息來源又只是坊間的網站,網民實在要多找幾個較具規模及公信力的新聞機構核實一下。
若最後發現消息真是捏造的話,也要有勇氣糾正錯誤,終止謠言。大家需要明白,新聞是建基於事實之上,趣味性只是附加的元素,這是不能逆轉的。即使再吸引的虛假內容,也只能是一個故事,一個笑話,而不是新聞。
其實,最大的笑話就是我們竟然沒有發現自己被人愚弄,而且任由愚弄我們的人擺布!
當傳媒積極介入社會運動
當傳媒積極介入社會運動,市民大眾就愈來愈難客觀、理性去討論問題。現時在社交網絡、甚至主流傳媒,作為受眾,我們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一時間很難分辨信息的真假,以及信息發佈者有沒有斷章取義,改頭換面、加鹽加醋。而作為信息接收者,我們亦容易出現一種主觀願望的偏見,對一些自己認同的信息傾向照單全收,對一些自己不認同的意見就以陰謀論、懷疑論來看待。近期林老師以粗口鬧警察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8月11日,特首梁振英到天水圍,收集巿民意見,就著政制民生究竟說了甚麼,傳媒沒有甚麼報道,因為大家的焦點都集中一位小朋友身上和林老師粗口事件的餘波。這位小朋友向著記者說自己受襲經過,有電視台將他的一面之辭播出來,但在衝突期間,其他記者亦先後拍到這位自稱受害人的小朋友,站在垃圾筒上做指揮,更手持膠樽,擲向反對他們聲音的人士身上。大家若只看一個報道,就很容易會被誤導。
近年傳媒生態大變,不少傳媒對社會問題,對政府和各政黨愈來愈有立場,已經將報道和評論混淆不清,往往在有意無意之間選擇性報道,亦有因為人手不足,為求交差,輕易採用網上流傳的資訊作為報道的根據。對於後者,這是個人操守問題,如果發現之前真的是誤報或者漏料,記者及管理層應該想辦法補救,不會容許自己的偏頗失真的報道不了了之。不過,如果問題是傳媒故意選擇性報道,對社會來說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本來市民大眾理論上應該相信傳媒每天會努力公正地報道新聞,將最重要的消息告訴社會,並由市民大眾根據事實去討論現時的社會問題,不過,眼見傳媒在把關上愈來愈多問題,不少人將希望放在公民記者身上,透過社交網絡、YouTube、facebook和網誌等方式將資料散播。
但是,瀏覽社交網絡的消息最大的困難是,我們沒有辦法知道他們的真確性。就以林老師在旺角以粗口向警方表達不滿為例,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角度拍了類似的情況,片段有長有短,亦有人懷疑內容有真有假,作為巿民我們未必有專業的知識去判斷片段是否經過加工,再者,這些片段中往往加入很多後期的剪接,其目的不是令人了解事實,而是一開始就加入個人意見,這類「消息」可信性比新聞更低,但其滲透的能力,有時卻比一般新聞更高。
本來要判斷這些網上資訊的真偽,應該依賴記者找當事人和專家求證,不過,當傳媒本身已有鮮明立場,往往刻意選擇性報道。加上在手機和互聯網大行其道的今日,社交網絡的消息與主流傳媒的新聞並存,似乎已經無法避免。作為受眾只能自求多福,多看幾份不同立場的報章,多看幾個電視台的新聞以作比較,當瀏覽網上資訊時要加倍小心,必須要用批判的方式閱讀,減少受到一些帶有偏見的資料和意見影響。
七一遊行 去不去也會被標籤
本地樂隊RubberBand幾經風雨,七一終於完成那個被惡名為「維穩」的「巨蛋騷」。樂隊成員穿了黑底白字寫「NO」的汗衫,之後再去七一遊行,又唱《睜開眼》,才能為樂隊挽回敢於批評社會的形象。
現在,不去遊行會被直接質疑是維穩,是支持建制。參加巨蛋騷的人,就即時被標籤為親建制,彷彿只有參加遊行的人才有資格支持民主。一個人不參加一個政治活動,可以有很多原因,但出席就只有一個原因——支持這個活動舉辦者所定的立場。
這種不參加某某政治活動會被標籤的狀態,近年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於五區公投後稱,該次立法會補選(即變相五區公投)投票率只有不足兩成,「所以」不投票的巿民全都是不支持五區公投。事實上香港選民的投票率,不論是立法會還是區議會選舉,整體投票率從來也只是五成左右,如此將沒有投票的選民歸邊,是不公道的。
支持個別政治議題的人將不必要的標籤強加在沒有參加任何活動的巿民身上,是非常無賴、非理性和不必要的。社運人士加上互聯網的推波助瀾下,持不同立場的人正在爭取不同人士的支持,但從前可以容得下的中間、理性聲音,現在卻漸漸失去立足之地。每當在立場及行動上與主要的社運方向不一致時,就即時被劃清界線。個別聲音不能發,或者發了之後,都只能跟社運「主旋律」的解讀方式,將你歸邊分類。
更甚者,有時我們參加了一個運動,也不知道最終我們的意見會怎樣被解讀。2003年,我們去七一,為的是反對廿三條和爭取0708雙普選。後來,七一遊行的訴求愈來愈多,議題愈來愈不單一,但民主普選的聲音仍然響亮。到今年,當你再看報章報道,不難發現七一已淪為各說各話的平台,這份報章說遊行是為了民生議題,那份報章卻說是為了叫梁振英下台,而據調查顯示,最多人關注的其實是爭取雙普選,但民意卻被一些報章各取所需地騎劫了!有報章甚至只報道激進行為。原本以和平遊行表達訴求的力量,漸漸消失。
遊行的議題愈分散,對政府的施政壓力愈少;遊行(或不遊行)的香港人愈被無緣無故的標籤,只會挑起他們更多對社會行動,或者以遊行等方式表達對政府看法的反感。我們珍惜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但當傳媒在遊行後第二天已經為各擺街站的社運組織和政黨「埋單計數」,看看哪個黨籌錢籌得最多時,我們不禁嘆息遊行在不少人眼中,已淪為社運組織及政黨等團體的大型籌款活動。
我們亦不禁問:爭取民主的人,為何舉辦一個遊行去將支持民主的人分散,或者將他們遊行的力量攤薄呢?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七一遊行?似乎是未來七一的重要課題。
公民記者抬頭 傳媒生態敲警鐘
要談香港的傳媒生態,除了傳統的新聞媒體外,不得不提「公民記者」。公民意識抬頭,加上智能手機普及化,香港人已很習慣把碰見的新聞故事即時拍攝或錄影下來,然後透過網絡平台發佈開去。與此同時,近年本港也愈來愈多由民間人士組成的「公民媒體」,它們在新聞發酵及加溫方面,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究竟隨著「公民記者」或「公民媒體」的發展愈趨成熟,香港的傳媒生態會有甚麼轉變呢?
以往,只有受過訓練的新聞從業人員才有可能採訪或製播新聞,但「公民記者」的出現,卻打破了這個傳統。事實上,近年由「公民記者」發掘出來的新聞,不少都成功帶動社會的關注,引起極大的迴響,記憶猶新的包括「巴士阿叔」、[1]「導遊阿珍」[2]等,連主流新聞媒體也爭相轉載報道。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教授在接受本刊訪問時表示,在新傳播科技的發展下,當具圖片、影像拍攝功能的手機愈來愈普及化時,「公民記者」的發展,將會是一個趨勢。然而,當「人人是記者」,網絡上充斥著大量的資訊時,傳統的新聞媒體便須要格外留神。
「現在香港的傳媒,很多時都會採用網民發佈的消息,有些報章甚至直接引述他們所說的作為新聞報道,我認為這樣的做法不太恰當,長此下去,會令我們新聞內容的質素有所下降。」
公民新聞易欠缺客觀性
這是由於在公民新聞當中,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親歷其境的事情,以第一身的形式去報道,那麼新聞的取態自不然是自己個人的觀點。梁教授認為,這種新聞內容往往有煽情成分,如果傳媒工作者,不去先作核實當中的真偽性,便草率地轉載報道出來,這是有違操守的。
「基於保障言論自由、資訊自由,雖然新聞法沒有說發佈假消息便要坐監,但作為受過訓練的傳媒工作者,我們要持有的操守,應該是高於法律之上。」
除了獨立的「公民記者」,近年香港亦有不少由民間人士組織而成的「公民媒體」,例如「主場新聞」、「獨立媒體」、「輔仁媒體」、「SocREC社會記錄協會」等,它們都號稱不受任何財團、政黨或政權支配,讓市民大眾都可以參與成為新聞資訊的發佈者,旨在打破社會單一化的言論和思考模式。
公民媒體影響力龐大
作為資深的傳媒人,梁天偉教授相信,有組織、有品牌的「公民媒體」比起獨立的「公民記者」將會愈來愈受到重視,他指出︰「『公民媒體』特別對Campaign(運動),例如是選舉運動、商業運動,有一定的加溫作用,像今次慢必(陳志全)能夠當選立法會議員,『公民媒體』就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
正因為「公民媒體」的影響力大,故他認為媒體中的記者也應該由受過訓練的傳媒工作者去擔任,這才可以建立起良好的品牌,美國著名新聞網站《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3]就是典型例子。
「所謂受過訓練,是指他有一定的操守,懂得傳媒的運作,懂得怎樣去表達或說服別人,這樣就會事半功倍。另外,專業的新聞工作者,也應該是抽離現場的,那才有客觀的報道、客觀的圖片,他們不會混在人群中,隨群眾呼喊口號、衝擊。」
可是,我們卻發現,近年香港的傳媒生態,不單是「公民記者」、「公民媒體」,就連傳統的新聞媒體,也犯上梁教授口中的「大忌」,所指的是經常性以第一身作主觀性的報道,令主流媒體也充斥著「立場新聞」。
提升下一代傳媒素養
梁教授直指這種發展並不健康。「以今次國教事件、市民在政府總部集會為例,《蘋果》在它的新聞版面,就經常用上『我們』這個字,這明顯不是單純的新聞報道,而是夾雜了評論。我就常以此告誡學生,專業的新聞,不應用第一身的方式去做。評論歸評論,新聞報道就應該純粹作出新聞報道,讓我們的讀者自行判斷分析。」
惟他歎謂︰「現在每當有消息傳出,傳媒就很喜歡幫受眾預先消化,然後再在新聞報道中直接告訴你該有的立場。不少香港人也很懶惰,他們看完那則新聞後,就往往會把傳媒的立場當作結論,這樣很容易有偏頗。」
面對這股風氣,梁教授坦言大勢難擋,他更預計,在可見的未來,意見夾雜式的新聞報道將成主流,作為傳媒教育工作者,他唯有從提升下一代的「傳媒素養」入手。
所謂「傳媒素養」,就是要讓讀者知道,每張報紙的立場是甚麼,知道它發放著怎麼樣訊息,而那些訊息又帶來甚麼結果。「當讀者看得通透,便知所警惕,不會被它牽著你走。而這個教育的功課,在小學、中學便要開始。」梁教授說。
公民記者不是私刑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