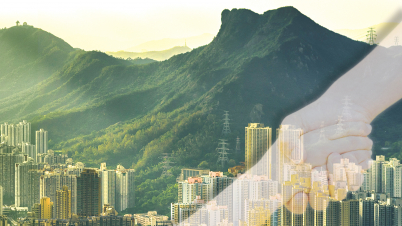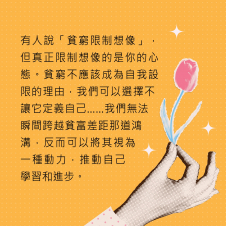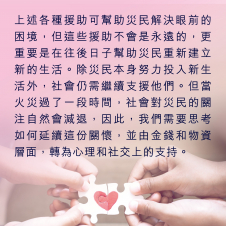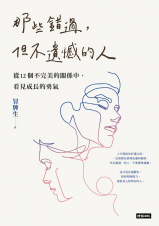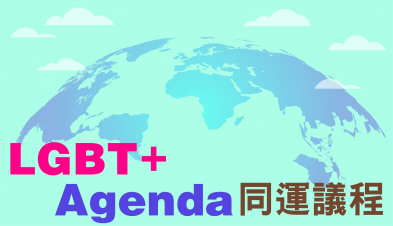- 引言
今時今日,相對文明的國家都會關注兒童的福祉,為保護兒童人權或利益而訂立相關的政策。現實中卻存有一些直接影響兒童的政策,未有嚴謹地查考或驗明對兒童的影響,卻為了順從或取悅主流就輕率通過,讓兒童承受後果,你對此有何想法?
隨著同性民事結合或同性婚姻在世界各地被承認,爭取同性伴侶領養權的呼聲可謂大勢所趨。在不少國家,同性伴侶是因其民事結合或婚姻的關係合法化,於是在法律上被默許取得兒童的領養權。不過,認同同性伴侶的婚姻,是否真的就順理成章認同他們擁有領養權?
- 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
支持同性婚姻的理據,主要認為同性戀關係中的成年人士,應該享有與異性關係中的成人相同的權利,而不應在婚姻法例中被歧視,這亦是某些國家給予同性伴侶領養權利的理由(例如奧地利、克羅地亞)。但是,有時我們可能會忘記,在領養法例中被牽涉的不單是成人,還包括兒童。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1] 在第21條,更明言「凡承認和(或)許可收養制度的國家應確保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如果立法機關只考慮到成年的同志群體在法律上應該取得平等地位,就默許給予領養兒童的權利,是否有以兒童的利益為優先考慮呢?[2]
當然,在同性領養合法化的國家中,亦不乏以兒童的利益作為理由(例如英國、希臘等等)。但值得留意的是,一些禁止同性伴侶領養的國家,同樣是以兒童的福祉為理據(例如匈牙利、波蘭等)。那麼,到底是容許的好?還是禁止的好?專家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作出有利於兒童福祉的決定嗎?
- 「沒有差異」已成定論?
過去有不少研究,指出在同性伴侶的家庭中成長的兒童,在各方面的發展都與一般家庭無顯著差異。但有學者重新審視過這些研究,發現這些研究都分別有樣本數量不足、取樣方式有偏差、在研究或論證過程上有謬誤等等的狀況,以致研究結果的代表性成疑。[3] 一位學者Douglas Allen重新評估其中一份支持同性撫養無差異的研究:“Non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Childhoo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4] Allen的團隊發現以原作者的分析方法,即使來自不同家庭模式的兒童之間有實際差異,都只會得出「無差異」的結果。當Allen重新計算其數據後,更發現異性家庭的孩子比同性家庭的孩子發展得較好的差異達到35%。[5]
在2018年,一位大學教授Walter Schumm出版了Same-sex Parenting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一書,當中對現存的三百多個與同性撫養有關的研究——不論結論是支持或是反對的——作出評估。一方面他指出了反對同性撫養的研究當中的限制和錯誤,另一方面亦在認為同性家庭與一般家庭無差異的文獻中發現了研究方法上的問題,甚至在它們的數據中找到可證明有差異的證據。他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現有的證據其實並不足以支持同性撫養「沒有差異」的論說。[6] 事實上,同樣有不少的研究顯示,同性家長及異性家長的撫養出來的孩童,確實在成長、發展上有實際差異,同性家庭中的孩子甚至在不同方面的發展都受到負面影響。[7]
研究的工作不免會有限制或疏忽,但學者們若能以其專業互相提醒,嚴謹地改進有錯謬的研究方法,亦必定能為社會帶來實際、有力的洞見。只不過,當現今的研究仍有如此多地方需要改進的同時,為何仍有主流的聲音紛紛將「沒有差異」視為鐵則呢?Schumm指出這些研究被引用,是因為它們「政治正確」,[8] 而他撰寫Same-sex Parenting Research一書的初衷,正是「不希望政治扭曲了科學證據」。[9]
- 「政治正確」還是謹慎驗證?
奈何在「政治正確」的驅使底下,有一些聲音卻似乎正受到主流排擠。Schumm在其著作中並沒有以其研究為理據對婚制作任何的評論,更明言他不希望他的研究成為同性領養被禁止的鐵證,他由此至終想強調的是科學的精神,但他仍因不接納「沒有差異」的結論,而被同行詆毀及排擠。[10]
除了Shumm,美國兒科醫生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下稱ACP)亦因「政治不正確」而受到排擠。ACP是一間無宗教信仰、無政治背景的機構,有六百多位醫生或醫科專家為會員,主力以科學及醫學知識宣傳促進兒童健康及福祉的資訊,或倡議相關政策,[11] 他們亦基於科學的理據提出與同運分子不同的意見,因而受到抨擊及排擠。如果在維基百科上搜索,我們只會看到ACP一些被認為是反同的言論,以及其他組織、機構對它的抨擊,在維基百科上它的定位甚至被描述為︰「該組織的主要關注為倡議反對墮胎及同性戀者收養兒童。」[12] 這其實與ACP所聲明的並不相符。[13] ACP關注的議題,還有醫學實踐、疫苗、安樂死、毒品的影響等等,[14] 遠不止於同志相關的議題,為何他們會被視為只關注反同的組織呢?[15] 它的主張或許仍有可以商榷的空間,但今天人們批評、排擠它的理據,是經過嚴謹的學術驗證,還是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
若我們是以兒童的最大權益為原則,我們就必須謹慎思考,絕不能以「政治正確」為前提,輕率地採納迎合主流的結論;既要追求謹慎,就應多方求證,在各方的理據中權衡輕重、利弊,既知道統計研究上會有限制,就需要學習分辨,平衡地審視正、反不同的資訊和意見,並要容讓不同的聲音存在,讓社會各界都有機會聽見及集思廣益。而這一點,是今天我們這個社會需要彼此共同努力的地方。
- 不同的家庭結構對兒童成長帶來不同的影響
那麼,在同性領養權這問題上,我們可以從何入手去考量兒童的利益?在這裡引述一份文章,希望為大家提供一個思考的角度。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這篇文章於2002年,由Kristin Anderson Moore等的數位學者及研究員撰寫,[16] 它研究家庭結構對兒童造成的影響,並倡議婚姻及家庭方面的改革政策。因為當年在美國全國調查的問卷上,尚未有同性家長的選項,所以它的議論並非針對同性撫養,也可以肯定這篇文章並不是為了支持或反對相關議題而寫的。
在這篇文章中,Moore等人透過文獻回顧,總結出不同的家庭結構確實會影響兒童,兒童與親生父母同住,並且在低衝突的婚姻關係的環境底下生活,這對兒童的成長是最好的。Moore等人亦提到,即使是有雙親,但其中一方是繼父或繼母的情況下,兒童的「幸福指數」(levels of well-being)仍然是相對較低的。[17] Moore的文章並沒有否定任何人士照顧兒童的能力及愛心,它帶出的是一個家庭的結構或模式對兒童的成長的確會帶來不同的影響。我們無法否認,同性的伴侶是無法同時成為同一個兒童的親生父親或母親,最起碼必然有一方並非孩子的親生父親或母親,或者雙方都不是親生的。那我們是否應該承認同性婚姻這種不同的家庭模式真的會帶來差異呢?
當然,Moore等人的研究也不會毫無瑕疵,亦不能為我們提供一個絕對的答案,但希望藉此大家能有多一個的思考方向。與其盲目相信「沒有差異」這信條式的偽裝,[18] 倒不如踏實地去檢視當中會產生的差異是甚麼?對兒童帶來的影響是甚麼?這才能真正找到對兒童最好的方案。
- 結語
有些人或者會以兒童的福祉為由,認為通過同性領養能讓一些有需要的孩童找到新家庭。我們也必須正視,現實中的確有一些家庭或婚姻是出現問題,以致某些兒童必須與他們的原生家庭分開,才能確保他們得到最大的保護。不過,容許同性伴侶獲得領養權卻不是唯一的辦法,許多國家早在通過同性領養前,已經有讓已婚的異性夫婦領養或寄養等的機制,以幫助有需要的兒童。再者,面對社會上的兒童或家庭的問題,我們要積極尋求的是治本而非治標之法。[19] 既然如此,當現存的研究仍然存在問題,而同性撫養對兒童的影響仍然存疑的情況底下,我們是否真的要貿然同意呢?
要考慮兒童最大的利益,或許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必然完善的方案,但正因沒有必然的答案,我們就更需要匯集不同的意見和聲音,再從中找出一個令兒童損害最少、受惠最多的方案。這些聲音不是為成人,而是為兒童而聽的,假若只順從成年人世界的主流喜好,而排擠另一方的論述,就會令我們錯過重要的信息,而承擔後果的卻是兒童。如果未經過嚴謹的考量,只為追求「政治正確」、跟隨主流,就將一眾兒童的福祉奉上作為賭注,你能接受嗎?
參考資料
〈打破「沒有分別」的迷思──論同性家庭撫養孩子的最新社會科學研究〉。《性文化評論》,第一期(2014年9月)。網站:http://www.scs.org.hk/comment/2014/Vol1/comment1.pdf。
〈應該如何解讀同性撫養的研究?〉。性文化資料庫,2016年11月25日。網站︰https://blog.scs.org.hk/2016/11/25/%e6%87%89%e8%a9%b2%e5%a6%82%e4%bd%95%e8%a7%a3%e8%ae%80%e5%90%8c%e6%80%a7%e6%92%ab%e9%a4%8a%e7%9a%84%e7%a0%94%e7%a9%b6%ef%bc%9f/。
招雋寧。〈關於同性撫養──不能不知道的最新研究〉。「明光社網站」。2016年9月12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E9%97%9C%E6%96%BC%E5%90%8C%E6%80%A7%E6%92%AB%E9%A4%8A%E2%94%80%E2%94%80%E4%B8%8D%E8%83%BD%E4%B8%8D%E7%9F%A5%E9%81%93%E7%9A%84%E6%9C%80%E6%96%B0%E7%A0%94%E7%A9%B6。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性文化資料庫。2019年5月31日。網站︰https://blog.scs.org.hk/2019/05/31/%e9%87%8d%e5%af%a9%e6%95%b8%e7%99%be%e5%80%8b%e7%a0%94%e7%a9%b6%e3%80%80-%e8%88%92%e5%a7%86%e7%9a%84%e3%80%8a%e5%90%8c%e6%80%a7%e6%92%ab%e9%a4%8a%e7%a0%94%e7%a9%b6%ef%bc%9a%e5%9a%b4%e8%ac%b9%e8%a9%95/。
陳婉珊。〈現時同性撫養(gay-parenting)的科學結論是甚麼?〉。性文化資料庫。2018年10月17日。網站︰https://blog.scs.org.hk/2018/10/17/%e7%8f%be%e6%99%82%e5%90%8c%e6%80%a7%e6%92%ab%e9%a4%8agay-parenting%e7%9a%84%e7%a7%91%e5%ad%b8%e7%b5%90%e8%ab%96%e6%98%af%e7%94%9a%e9%ba%bc/。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Accessed 14 July, 2021. https://acpeds.org/about/faq.
“Our Position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Accessed 14 July, 2021. https://acpeds.org/positions.
“Topic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Accessed 14 July, 2021. https://acpeds.org/topics.
Michelle Cretella, and Den Trumbull, “Homosexual Parenting: A Scientific Analysi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Last modified May 2019. https://acpeds.org/position-statements/homosexual-parenting-a-scientific-analysis.
Allen, Douglas W. “High school graduation rates among children of samesex households.”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13). http://mcadams.posc.mu.edu/blog/gay_parenting.pdf.
Allen, Douglas, Pakaluk, Catherine Pakaluk and Joseph Price. “Non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childhoo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 A comment on Rosenfeld.” Demography 50, no.3 (2013): 955–961.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2-0169-x.
Cretella, Michelle, and Den Trumbull. “Homosexual Parenting: A Scientific Analysi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Last modified May 2019. https://acpeds.org/position-statements/homosexual-parenting-a-scientific-analysis.
Lerner, Robert, and Althea K. Nagai. No Basis: What the Studies Don't Tell Us About Same Sex Parenting. Washington DC: Marriage Law Project, 2001.
Moore, Kristin Anderson, Susan M. Jekielek, Carol Emig and M. P. P. June.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Child Trends Research Brief (June 200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7432167.
Regnerus, Mark. “How different are the adult children of parents who have same-sex relationships? Findings from the New Family Structures Stud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 no.4 (July 2012): 752–770. https://doi.org/10.1016/j.ssresearch.2012.03.009.
Rosenfeld, Michael J.. “Non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childhoo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 Demography 47, no.3 (2010): 755–775. https://doi.org/10.1353/dem.0.0112.
Schumm, Walter R..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Research on Same-Sex Parenting and Adop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9, no.3 (September 201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8043861.
Sugden, Chris. “Same-Sex Parenting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 Oxford Centre for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Last modified March 15, 2019. https://www.ocrpl.org/same-sex-parenting-research-a-critical-assessment/.
Sullins, D. Paul. "Invisible Victims: Delayed Onset Depression among Adults with Same-Sex Parents." Depressio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2016 (2016). https://doi.org/10.1155/2016/2410392.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Wikipedia. Last modified 4 June, 202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College_of_Pediatricians.
[1]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1989年11月20日,網站︰https://www.cmab.gov.hk/doc/tc/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the_rights_of_the_individuals/crc.doc(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3] Robert Lerner, and Althea K. Nagai, No Basis: What the Studies Don't Tell Us About Same Sex Parenting (Washington DC: Marriage Law Project, 2001); Walter R. Schumm,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Research on Same-Sex Parenting and Adop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9, no.3 (September 201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8043861; Michelle Cretella and Den Trumbull, “Homosexual Parenting: A Scientific Analysi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last modified May 2019, https://acpeds.org/position-statements/homosexual-parenting-a-scientific-analysis.
[5] Allen的團隊以原作者Rosenfeld的方法重新比較過其數據,發現以該方式來計算,不單是同性撫養的家庭與異性撫養的家庭比較起來無差異,甚至相比其他家庭模式,例如未婚媽媽的家庭亦無法測出差異,而過去眾多學術文獻都證實不同家庭模式的兒童發展是有差異的。Allen亦重新評估過Rosenfeld的統計方法,發現以其方法計算的話,即使比較結果的差異大到接近50%,依然只會得出「沒有差異」的結論,這表示「沒有差異」的結論是不可靠的。此外,Rosenfeld為了提高孩子成長環境穩定性,只計算了戶主的親生孩子(即排除戶主領養或繼養的孩子)及五年內都居於同一處所的家庭,但這一來排除了家庭結構及住所不穩定性這些對孩童有實際影響的因素,二來亦減少了超過一半的樣本數量而削弱其代表性,當Allen將被排除的樣本重新加入評估,並對個人及家庭的社會經濟因素加以控制,發現異性家庭的孩子比同性家庭的孩子發展得較好的差異達到35%。參︰〈打破「沒有分別」的迷思──論同性家庭撫養孩子的最新社會科學研究〉,《性文化評論》,第一期(2014年9月),頁5-6,網站:http://www.scs.org.hk/comment/2014/Vol1/comment1.pdf(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Allen團隊的研究︰Douglas W. Allen, Catherine Pakaluk and Joseph Price, “Non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childhoo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 A comment on Rosenfeld,” Demography 50, no.3 (2013): 955–961,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2-0169-x.
[7] Mark Regnerus, “How different are the adult children of parents who have same-sex relationships? Findings from the New Family Structures Stud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 no.4 (July 2012): 725–770, https://doi.org/10.1016/j.ssresearch.2012.03.009; D. Paul Sullins, "Invisible Victims: Delayed Onset Depression among Adults with Same-Sex Parents," Depressio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2016 (2016), https://doi.org/10.1155/2016/2410392; Douglas W. Allen, “High school graduation rates among children of samesex households,”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13), http://mcadams.posc.mu.edu/blog/gay_parenting.pdf. 有關Sullins的文章,可參考︰招雋寧︰〈關於同性撫養──不能不知道的最新研究〉,「明光社網站」,2016年9月12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E9%97%9C%E6%96%BC%E5%90%8C%E6%80%A7%E6%92%AB%E9%A4%8A%E2%94%80%E2%94%80%E4%B8%8D%E8%83%BD%E4%B8%8D%E7%9F%A5%E9%81%93%E7%9A%84%E6%9C%80%E6%96%B0%E7%A0%94%E7%A9%B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9]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
[10]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
[17] Kristin Anderson Moore et al.,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18]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
[19] 雖然家庭政策並非本篇的主題,但在Moore的文章裡,也有一些透過社會政策改善家庭結構的提議,讀者若有興趣可以參考,Kristin Anderson Moore et al.,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