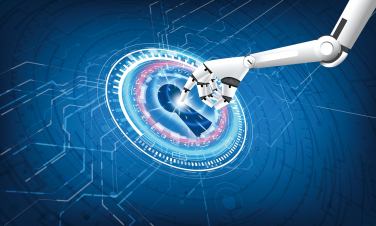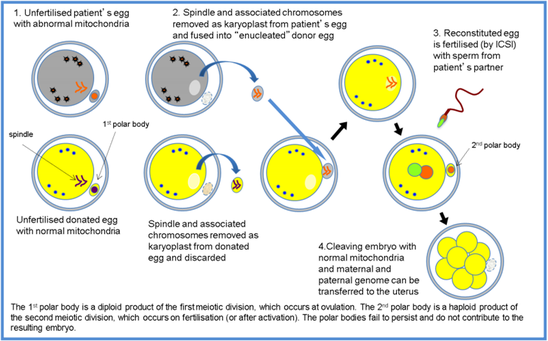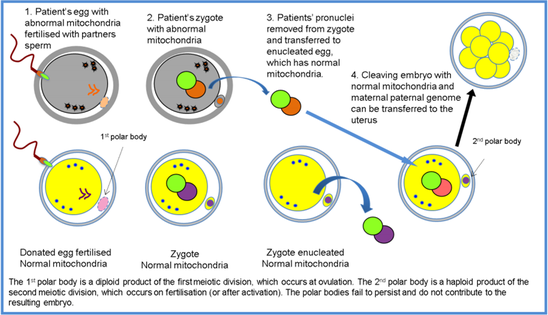人普遍認為自己有選擇權,選擇買甚麼、吃甚麼、喝甚麼和穿甚麼。整個過程就是,看見自己想要/需要的東西,然後選擇購買,這看似是人的自主選擇,但事情果真如此嗎?自網絡的出現,人能夠自主選擇的機會已經逐漸減少,現在,人所作出的選擇,其實很大程度受到人工智能(AI)和演算法的操控和引導。這是否就意味著,人再無法作出選擇?答案是「否定」的,人仍能夠選擇是否遵從人工智能的建議,但人性真的允許人類這樣選擇嗎?筆者嘗試分析網絡大數據如何影響人的選擇,再推進至人如何自主地放棄思考,自願地被人工智能控制。
網絡世界中的自主與抉擇
有關大數據和演算法如何影響用戶使用網絡,可參閱本社過往推出過的文章。[1] 提到大數據,必然令人聯想到Google,以香港的情況,基本上沒多少人能脫離使用Google,無論搜尋甚麼資訊,這個強大的數據庫,總能提供豐富資訊,相信現在使用Yahoo以及Bing來搜尋資訊的人,只屬少數。之不過,強大的數據庫其實也代表著它會從中學習,分析用戶的網絡使用習慣以及常輸入的問題,並且能得出相當精準的推算結果,也就是說,用戶透過手機、電腦或網絡獲得的資料、留下的消費及搜尋記錄、發出的電郵與簡訊,都赤裸裸地揭示了自己。
《連結之戰:網路、經濟、移民如何成為武器》一書中,記錄了不少受大數據影響的例子。作者里歐納德指出,當Google以用戶的搜尋記錄作為線索,它可能比當事人更早知道自己懷孕了,這都是一些非常精準的數據分析,換言之,Google也有能力決定用戶看哪些資訊、聽哪類人說話,或作出一些它能夠預測到的行動。[2] 最生活化的例子就是當用戶在網上搜尋想要買的物品後,就會發現在許多軟件、網站、社交媒體中,都會出現曾經搜尋過物品的廣告,這些資訊不斷出現,一再勾起人的欲望,買下它們只是時間的問題,這就是能夠預測到的行動。若然遇上這種情況,廣告的出現自然不是上帝給人們的印證,而是代表人們在「迴聲室」(echo chamber)遊走罷了。[3]
大約在10年前,Amazon嘗試使用人工智能來篩選應徵者的履歷,它從100份履歷中篩選出最適合的五份履歷,Amazon隨後就會僱用這五位應徵者。但後來有人發現,這個理性的人工智能竟然因為過去獲聘的人以男性居多而自動將女性應徵者的履歷排除在外。由此可以預視到,若由理性的人工智能「統治」世界,為了減少碳排放量,對它來說最有效率的方式,可能就是將人類排除在外。[4]
人是失去了,還是放棄了思考?
從人工智能不斷收集數據開始,人似乎難以躲避「迴聲室」造成的影響,單一的資訊吸收渠道,令人無論對電影、時事或政治的觀點,都失去了容納差異的器量,這是否代表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人類無法自主思考已經成為不能逆轉的事實呢?理論上不是,但實際上人往往自願地配合人工智能,因為人很容易聽自己想聽的說話,看自己想看的事物。在這裡筆者嘗試透過現代社會的文化講述當中的道理。
比起變幻不斷,人更喜歡萬事萬物掌握於自己手中,對他者也是如此。近來無論在海外抑或本地都非常流行16型人格測試(MBTI),基本上,不少大學生或青少年在認識朋友時,都會以MBTI作為參考,以掌握對方的性格,MBTI測試的結果亦常見於交友軟件的個人介紹中。曾經有人對此現象作出分析,並將文章在一份期刊發表,當中指出,許多人與朋友交談時,都會聽到朋友提及MBTI,而一些公司在聘請員工的時候,都會要求應徵者做MBTI測試,看看他們是否適合應徵的工作崗位。[5] 除了MBTI,在未信主的群體中,不少人亦沉迷於12星座的性格分析,好像只要知道一個人是甚麼星座,就能夠得知他是甚麼性格,而且更不需要填任何心理分析的問卷,換言之就像是每一個星座對應某些性格特質。
不過,無論是透過MBTI或12星座來認識一個人,其實都是嘗試將對方掌握於自己手中,即將人歸納為16種或12種性格;不過,人的獨特性與無限性不是單單靠心理測驗或星座便可以解釋。例如在MBTI中有16種性格,但似乎要區分及理解16種性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當中的一項指標依照人的性格傾向,將人歸類為「E人」(外向)或「I人」(內向),這樣簡單的分類,正是消除身為一個「人」的無限可能。[6] 人變相不想探索不同人的不同面向,甚至透過MBTI或星座來篩選誰人適合交往。
在觀察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玩電腦或手機遊戲時,也能看到其實人很多時都自動放棄思考。筆者是電子遊戲愛好者,也會加入一些相關的臉書社群與他人交流,或接收遊戲的最新資訊。不少人往往很喜歡將遊戲攻略貼到臉書上,也會為到自己完全跟上攻略的指示以致勝出而感到自豪。但遊戲的本質正正是要玩家自己發掘能夠贏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只為了得到「贏」這個結果。
希望「不勞而獲」或付出一點兒努力就得到想要的結果,這類想法正好反映了人性。若然人們只仰賴已有的分析結果,而不嘗試花時間理解他人,和不嘗試為自己的興趣付出努力的話,其實人們是在放棄思考;當人們自願放棄思考,不選擇「不遵從」一些既有的建議,到最後人類全然地被人工智能取代也可能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人們喜歡高舉理性,所以選擇人工智能,因為它能夠做最理性的決定,但惟有「非理性」才顯得一個人更像人。
(本文原載於第159期〔2024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蔡志森等編:《網絡激流攻略》(香港:明光社,2023),頁38–40、45–49,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flipbook/misc/book25(最後參閱日期:2025年8月21日)。
[2] 里歐納德〔M. Leonard〕:《連結之戰:網路、經濟、移民如何成為武器》(The Age of Unpeace: How Connectivity Causes Conflict),王眞如譯(台北:行人,2022)。
[3] 佐佐木俊尚:《智慧型手機知識碎片化時代的「閱讀力」最新技術大全:把現代病「無法集中」轉為個人智能,「輸入」與「輸出」最大化!》,林巍翰譯(新北:方舟文化,2022)。
[4] 里歐納德:《連結之戰》。
[5] Jingyi He,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Popularity of MBTI Personality Tests,” Advances in Social Behavior Research 5, no.1 (January, 2024), 1–4, https://doi.org/10.54254/2753-7102/5/2024036.
[6] 施羅撒:〈他者倫理學之主體的誕生〉(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頁38,網站:https://nhuir.nhu.edu.tw/retrieve/21101/101NHU05259017-001.pdf(最後參閱日期:2025年8月21日)。